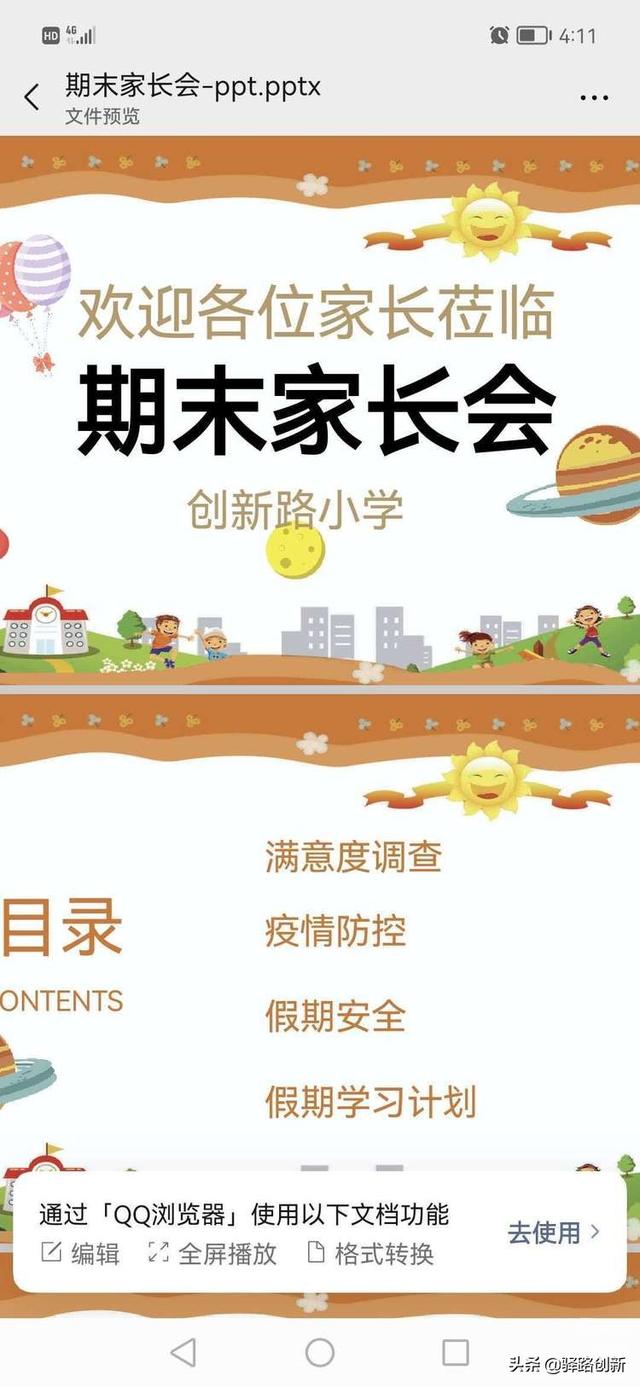说到六一国际儿童节,大概没有几个人明白它的由来。实质上,这个节日和纳粹军官——盖世太保头子海德里希的遇刺有极大关系。
1942年5月底,海德里希赶赴捷克古城布拉格,准备和希特勒本人碰头,商讨战争中的屠杀计划。赶赴会场途中,海德里希遭遇七名“纳粹猎杀者”的伏击,送往医院后虽然全力抢救,最终仍旧因伤重不治而殒命。
希特勒折损一员大将,因此极为恼怒,在围剿了七名伏击者之后,因为一封来历不明的信件,将目标锁定为距离布拉格五十公里之外的利迪策村,于6月10日对该村展开了一轮轰炸和屠杀,甚至连村中的坟墓也没有放过,尽数加以破坏,试图将这个村庄从地图上抹去。
战后清点,整个村庄只有当时外出的17人幸免于难,其余的所有人均死于这场灾难,包括全村的一百多名孩子。
为了让所有人记住这一桩惨案,不至于重蹈军国主义的覆辙,每年的六月一日就被定为国际儿童节,并流传开来。
不知道是不是自媒体大行其道的缘故,现在的学校特别热衷于一些外宣活动——不管别人看不看,反正自己就是要制作一些华丽丽的美篇和公众号。
我想,这些美篇和公众号,它们的命运大概率和纸质报纸的命运别无二致,不会有什么人感兴趣。但是,你又不能说它是负能量的东西。
虽然它的制作过程让老师们劳心费力,充满了怨气和戾气,整个制作过程充满了负能量,但在制作完成之后,谁能说这是负能量????
有的外衣就是外衣,你无法质疑。
关于这种美篇和公众号的制作,有一个演变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教师们没有接触过这么一种事物,还有一种淳朴的情愫,像小孩子一样,对它充满了懵懵懂懂的好奇。
那个时候的老师们大概以为:自己在一个学期之内制作不了几回,也参与不了几次摆拍,不会占用大量的工作时间。作秀就作秀吧,反正没什么好处,也没什么太大的坏处,就当是生活的一种调剂。
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教师中的一部分中等层级的教师慢慢喜欢上了这种工作,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显得自己整天都在忙碌,在BOSS面前有居功的资本:我为你粉饰了妆容,积攒了向上的资本。
如此一来,美篇和公众号就渐渐多了起来,分配给每一个在一线工作的教师的任务也多了起来,由他们在课余时间制作完成。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渐渐成了一个系统工程,要求越来越苛刻,制作越来越美轮美奂、图文并茂。制作次数也渐渐多了起来,要不了几天就会轮到自己一次。
每到自己制作的时候,教师就化身成了一名记者。在摆拍的时候,必须要抓拍到完美无瑕的照片和视频,保证没有每一个人出现在该出现的位置;进而,还要对海量的照片进行海选,保证校内掌控话语权的老师都能够出现在“大制作”里。
这个时候,考验教师“情商”的时机开始出现——搞错一个镜头,放错一个位置,就可能引来BOSS群体或者教师群体的质疑:你是不是有意捉弄我?你是不是有意贬损我?
教师群体的金字塔概念越来越浓厚,铜墙铁壁,壁垒森严。
这是空穴来风?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学校,已经因为这种美篇和公众号的制作不周,老师之间闹过好几次轩然大波的矛盾了,几近于全武行。(这一件事情,我以前提过,这里不再赘述,今后有的是时间,我可能会再次记述。)
当然了,在制作过程之中,制作人还免不了受到BOSS群体的耳提面命、反复申斥:“这点任务你都完成不了?这点任务都不合我的心意?!”如果没有一点心理承受能力,如果还保持着文人的儒雅谦和,一定会“可怜白发生”。
这些外宣材料制作出来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大用处,反正,我是从来不会翻看的——太浪费流量了。我更明白一点: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凡是展现在你面前的漂亮优雅,往往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月亮背面有什么,你往往意想不到。
可是,为什么我们又对这种制作乐此不疲?
最重要的一点:这些外宣材料就是学校BOSS的功绩,可以在BOSS的BOSS面前收获青眼。至于这些事情是否真实,效果几何,没有人会去深究。
此外,这些外宣材料制作出来之后,很容易批量下载。下载之后,各种各样改头换面,再打印出来,可以装入到堆积如山的蓝色塑料盒子之内,再摆满一个个铁皮柜子,依靠这些支撑起一个个学校的外壳。
说了这么多,主题就是一个:我们要制作对应的美篇和公众号,所以必须进行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展演。
这种展演的附带惊喜是:可以邀请学校之外的BOSS,让他们“驾临”欣赏,中午时候顺带去吃个便饭。
有没有不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折腾儿童、折腾普通老师的例子?
我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亳州某幼儿园在六一节期间,不再组织孩子们表演节目,而是别开生面地让孩子们们围坐一起,兴致勃勃吃了一顿饭。
在我看来,这样的六一节才是学生喜欢过的六一节,才会真正给学生留下美好的印象,而不是挑出十分之一的学生,冒着酷暑,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地去表演节目:辛苦自己,讨好别人,过成了成年人的“六一儿童节”。
毫不客气地说,学生们甚至无法看到所谓的节目,为了保持纪律,他们只是顶着大太阳,忍受着针刺一样的阳光,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看着前面同学的后脑勺罢了。
老师们呢,她们会全副武装的同时,找个荫凉的地方躲起来。
你如果问:“你躲到荫凉地里了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我全程都陪着学生学生坐在太阳地里,不带一丝防护。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会觉得自己亏欠了学生什么,心中很是不好受。
正是因为我这么做了,我才敢跟你说:阳光像针刺一样!
附带说一句,正是因为我的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我的同行对我极端排斥,他们会阴阳怪气地说我“不合群”、“孤僻”,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圣人蛋”——说到底,我这种做法与她们对比,很容易让她们觉得不舒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节目表演完毕,一则美篇或者一个公众号文案就已经出笼,教师群体中的既得利益者们欢欣鼓舞,甚至还可能拿到各种各样的辅导奖——不要忽视这样的辅导奖,在教师晋升职称的时候,这些东西非常有用,属于杀伤性武器。
讲一些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时的前奏吧,管中窥豹,从中看一看我们的教师多么“光明正大”。
我们这个年级组,老师们在“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状态下争取来了一个表演节目的机会——原本,老师们骂骂咧咧地不愿意参与表演,直言这种劳神费力的节目非常无意义;等到学校BOSS真的不让表演时,老师们再次开始骂骂咧咧,说“BOSS是‘dog的眼看人低’,不给我们年级组一个机会”。
不知道是不是某个“锦衣卫”把这种情绪告知了BOSS,BOSS再次允准本年级组可以编排一个节目,上台展演。
老师们展示完什么叫“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之后,办公室内掌握话语权的老师开始暗戳戳地詈骂:“排练节目不是一个人的事,所有办公室老师都要参加。”——这是她们的规定性动作:不攻讦别人就觉得少了点什么,总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假想敌,骂上一骂。
我们办公室只有六个人,其中三名是班主任,每个月多拿了六百元额外补助(是我月工资的五分之一)。从这一点上来说,排练节目就是她们的活计。
并且,如果这些节目获奖,荣誉证书上也是她们的名字,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会咬的狗,总能多吃到几块肉,不是吗?我向来不喜欢参与这些江湖纷争:抢到头破血流的荣誉,我内心里就特别想离得远远的。
除去三位班主任,本办公室的另外两位老师,都是情商极其在线、没事儿就骂一骂如同“挚爱亲朋”一样的同事的人中龙凤。她们和这三位班主任的交情,不敢说出则同辇、夜则同眠,但从蜚短流长的程度来看,几近于耳鬓厮磨。
毫无疑问,詈骂所指的对象就是我——在乌鸦的地盘上,白天鹅当然就是一种罪。
平时,每当她们把学生从正在上课的课堂叫出去排练的时候,我总是在上课。
面对他们的突然闯入和大声吆喝,我从来不会表现出什么不高兴:必须尊重自己的同事嘛,老实人不能主动找毛病,老实人就该逆来顺受,不能恶意揣测同事。
当我不上课的时候,分散在整个年级(三个班)里的学生又总是不再排练了。如此一来,我连表现自己的机会都没有。
不用怀疑,学生们对着大屏幕练习舞蹈的时候,我没有搬上一把椅子坐在旁边,我就是不热心集体事务的薄情寡义之辈,就应该被我的这些“可爱”的同事们恶意攻讦。
没办法,我特意调换了几节课,让我的“挚爱亲朋”先上课,自己去“看着”学生跳舞。
我特别声明:这一次我去,大家都不要去了吧!
结果,这老几位教师相视一笑:哎呀~,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一起去就一起去。只是,我表露自己功劳的机会又失去了。
到了所谓的舞蹈教室,这二位老师(一男一女)搬了一把椅子,旁若无人地坐在一起开始交头接耳,我则像一个机器人,傻呆呆地站在学生旁边——我根本没有一点舞蹈细胞,也指导不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从来不喜欢呵斥学生,在她们连珠炮呵斥学生的时候,经常有种汗流浃背之感。
当然,她们在无端呵斥之后,更多时间是不顾炎夏,聚在一起热议。
不是我特意去窃听,大概赖我的耳朵,那些故意压低的声音总能被我听个大概。她们说:“某某老师整天文绉绉的,真是个圣人蛋!”
“某某老师特别孤僻,不合群!”
“某某老师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完全不和我们谈闲话,不唠唠家长里短,一定是心理有问题!”
我简直躲无可躲——拍屁股走吧,不合适;听着吧,也不合适。
我在内心里想:什么时候,教师的“文绉绉”成了一种罪?
什么时候起,教师之间开始流行“码头”了,这些人一定要加入你的码头才行吗?
你们的所谓家长里短是什么意思?不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甚至不介意夫妻之间的关灯之后动作吗?
你们的所谓聊聊天,不就是教师之间的各种攻讦和各种“认码头”形式的认祖归宗吗?
她们在盼望着什么?不就是盼望教师群体之间形成一个个类似于三哥那样的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般的金字塔建构吗?
这么一来,我们的教育形势到底是一片大好,还是危若累卵?
举个梨子举个梨子吧,苹果太贵,我举不起。
不要觉得教师群体之间风平浪静,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教师群体的劣根性,从来都没有风平浪静过。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在那个知识匮乏的年代,这种学历已经等同于现在的一本,甚至可能还高于一本。
毕业之后,叶圣陶进入了苏州言子庙小学任教。
这个学校只有四名教师,但其中的倾轧仍旧纵横交织,波谲云诡。
叶圣陶曾经给当时尚在清华求学的好友顾颉刚写信,说自己不习惯教师之间的尔虞我诈,终日苦闷,课余在市场上看到补鞋匠,觉得没有人家自由自在,就特别想大哭一场。
如果是我有此感想,那些“高屋建瓴”者一定会抱着“扶不扶”的心态对我进行有罪推定:摔倒的老人和你,一定是你撞倒了老人!
可这里的主人公是叶圣陶,是我们教育部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你又该怎么认识?
你可以去翻翻叶圣陶的履历,他在1912年进入只有四名教师的苏州言子庙小学,经历了两年的苦闷生活,甚至还为此生了一场大病。在他大病未愈时,他的同事就为他设下了一系列陷阱。
叶圣陶没有识破这个陷阱,为了保护自己的自尊,他选择了离开,赋闲在家。
当然,因缘际会,后来的叶圣陶到了商务印书馆的旗下,才开启了另一段人生。
众所周知,叶圣陶的成名作《倪焕之》是对那个时代的控诉,但我看完叶圣陶的经历,总觉得他也在其中,也表达了对教师群体“相煎何太急”的劣根性的愁苦。
二十四年风尘岁月,信念好像还在我的心中。
二十四年的教学生涯,我看着教师群体的形象慢慢失去了光辉;二十四年来,我好像一直没有让自己尖刻,并且富有心机起来,这是我的失败。
不过,没什么可遗憾的:前路有光,初心莫忘吧。
上面是一个教师每天习惯性的闲言碎语,是纾解每天郁闷的一杯文字烈酒,未必合各位的心意,见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