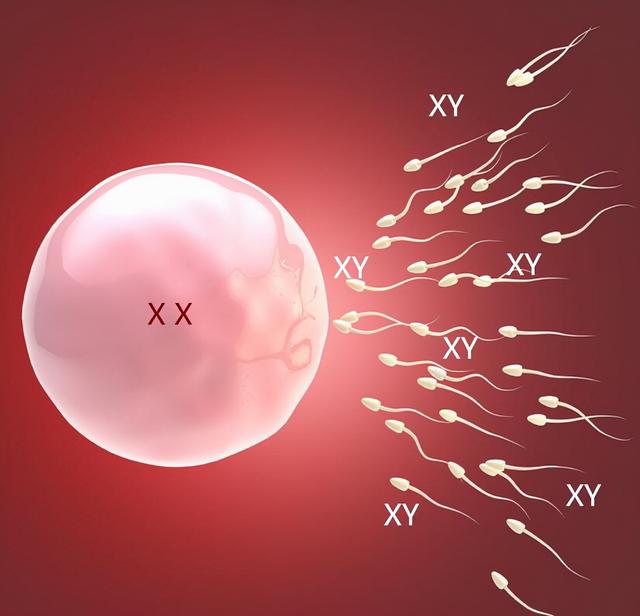寂静深夜,突然想起了子猷与子敬。
王徽之与王献之大约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兄弟之一,他们都是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一个家中老五,一个老七,年龄相近,自有父亲和哥哥们呵护,可以无忧无虑长大。相同环境下,志趣爱好也极为相投,比如他们都爱山水,喜欢清谈,擅长书法,似乎对做官都没有太大兴趣,行事作风也有相似之处——例如都曾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跑到别人家园子里,被锁在园子里还旁若无人。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埽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王更以此赏主人,乃留坐,尽欢而去。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之十六》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傍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人,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之十七》
虽是跑到别人院子里气死了主人,子敬和子猷风格还有些差别,子猷死猪不怕开水烫,一点也没把园主当回事,知道被反锁了,倒反而欣赏起这个得罪自己的人来了,也不怕这个时候才见面会跌份丢面子,大喇喇地一起喝酒尽欢。而子敬了,从头到尾将山水以外的世界彻底屏蔽,颇有些就是瞧不起你的味道,终于惹怒了将园主顾辟疆,把他“叉”了出去。
这大约是他们的不同,活在自己世界里的王徽之完全听凭自己的心意,行为处事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可以称之为“凉薄”。而王献之了?那份同样的不羁当中,似乎多多少少有些矫饰的成分,总不如子猷那样天真。也难怪欣赏他的谢安会说他“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当然,在宰辅谢安看来,王徽之大约就该是轻浮不堪重用了,问题是,子猷要的就是“不堪重用”,也算得偿所愿。)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己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
——《世说新语忿狷第三十一之六》
王羲之七个儿子,兄弟虽多,时常黏在一起的却唯此两人。他们的几位兄长,例如王凝之,就显得昏懦迟钝,不通世情,一心沉浸在宗教世界里,信得迷狂愚昧。王涣之王操之王肃之等其他兄弟,少有记载,纵有零星半点,表现得也是世俗平庸。只有子猷子敬之间,颇有些微妙的化学反应。时人也就不免经常拿这两个人互相比较:论容貌,“风流为一时之冠”的子敬肯定大大胜过哥哥;说到王家家传绝学书法嘛,王献之高出一筹;提到才情,也以子敬为尊;就连性情的比较,时人对子敬的评价也好过子猷不少。例如当子猷子重子敬三兄弟同时拜见谢安时,谢安明确表示说话少,不冷不淡的子敬最出色,因为“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之七十四》
另有一次,子猷与子敬一起在房间内时发生了火灾,子猷吓得跳起来马上就跑了,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但子敬却慢慢吞吞,面不改色,甚至召唤来左右侍从,搀扶自己走出房间,和平时一点也没有不同。在注重风度的魏晋,世人自然都认为,子敬胜过子猷。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发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唤左右,扶凭而出,不异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之三十六》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谁比谁强似乎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对这两兄弟来说,都是“who care ?”他们本来追求就相隔甚远。王献之崇尚高洁的人品,但子猷却更希望“慢世”,玩世不恭,“卓荦不羁”,不拘世俗礼法。这两种处事态度,无非是机缘与个人选择而已,很难说哪一种更占上风,就像同样的擅闯园子被人轰走,两人的应对却有细微不同一样。追求不同,让看似相近的两人性情也有很大的差别:较之哥哥,王献之更入世一些,始终抱着一种优游的态度应对官场。也因此受世俗牵绊更深,更不得已与自己心爱的妻子郗道茂离婚,另娶公主以完成家族使命,即使他曾经以烫伤自己的脚来表示反抗。自然,他的官位也因更容易妥协而更高。而王徽之了?简直生来就对拘束自己的外物深深厌倦,把官场当游戏,把领导当猴耍。问他做官都干了什么事就留下一千古名句“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西山吹来的风真凉爽啊!)下雨立即躲到领导的车里还振振有词:“您怎么能独自占有一辆车了?”更不用提他对自己的职务与工作内容一问三不知,“不知马,何由知数!”“未知生,焉知死!” 还喜欢时不时撩拨一下当时名士,干点小偷小摸吆三喝四爱答不理尖酸刻薄的事,所以世人都“钦其才而秽其行”,大抵就是嫌弃王徽之为人自我为中心,太过傲慢。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赏《高士传》人及《赞》 ,子敬赏井丹高洁,子猷云:“未若长卿慢世。”
——《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之八十》
王徽之的奇闻轶事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之四十九》
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 !”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之十一》
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
——《世说新语·简傲第二十四之十三》
苻宏叛来归国,谢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无折之者。适王子猷来,太傅使共语。子猷直孰视良久,回语太傅云:“亦复竟不异人。”宏大惭而退。
——《世说新语·轻诋第二十六二十九》
王子猷诣谢万,林公先在坐,瞻瞩甚高。王曰:“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林公意甚恶,曰:“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之四十三》
温和从容,高洁优雅的王献之虽然更能赢得世人的称誉,却没有获得个人的幸福,以至于数十年临终前还念念不忘被迫离婚的遗憾。而躁动不安的王徽之了?“雪夜访戴”的他不管被世人如何讥讽,大约都拥有了自己想要的一生。遵循本心遭人讽刺却无所顾忌的活一辈子,还是高官显达才情尽显却终身遗憾,说到底,还是个人的选择。
当然,两人对于人生方式的选择不同,以及世俗之人整日对两兄弟的品评,并不会影响到两人相知相交的程度。我想,子敬是非常欣赏也非常了解自己兄长的。他曾经写信给哥哥,说你生性凉薄,和流俗格格不入,真没什么好,但一喝酒就酣畅淋漓,甚至忘记回家,就这一点,还蛮可以值得骄傲。这夸奖,对常人而言也许不以为然:会喝酒,还喝得烂醉忘记了回家的路,只能算酒鬼一个!但这正是两人心灵的契合之处:子敬欣赏的是人情冷漠、遭人非议,爱喝酒又爱撒酒疯的子猷那份矫情纵性,能够在这个乱世不顾一切,一往情深地活着。
子敬与子猷书,道:“兄伯萧索寡会,遇酒则酣畅忘反,乃自可矜。”
——《世说新语·赞誉第八之一百五十一》
“慢世”的王徽之大约很为这番评价感到洋洋得意吧?整个世界对他的不耻有什么关系?“萧索寡会”又关天下人何事?能得到弟弟的“乃可自矜”的夸赞,已经是“吾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的他得到的最有力支持和回应。这样的回应,只关乎直觉,只关乎美,只关乎心灵。
他们是真的理解彼此!
所以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让他惦念不忘的,只有弟弟。史书记载,他在病榻垂危之时,曾对号称有让人代替生死法力的术士请求,我的才情官位都不如我的弟弟,我愿意把我的余下的生命都给他而自己死去。
对于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才会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了?至死不渝,生死相托。
后为黄门侍郎,弃官东归,与献之俱病笃,时有术人云:“人命应终,而有生人乐代者,则死者可生。”徽之谓曰:“吾才位不如弟,请以余年代之。”术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余,得以足亡者耳。今君与弟算俱尽,何代也!”
——《晋书·王徽之传》
没有多久,子敬就去世了。
王徽之前去吊丧。
没有眼泪,没有悼词,没有凄凄惨惨,没有撕心裂肺。
当王徽之知道自己的弟弟去世后,子猷异常平静的先是问左右:“怎么都听不到任何关于子敬的消息了?他一定是去世了。”语气当中,没有丝毫的悲痛。
是的,王徽之确实是个生性凉薄的人,他对这个世界在乎得实在太少了,他对生死的看法,也和大多数人都不一样。
他或许真的是那个,对除了自己感受以外任何事情都会无动于衷的人吧。
面无表情的他立即前去奔丧,一声也不哭,在灵堂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子敬平时喜爱弹奏的琴,想弹奏一曲。常人很难明了他此时的心境——没有眼泪,没有哭泣,没有语言……直到他发现琴弦音调不准,千般情绪顿时涌上心头,化作了一声永恒的咏叹“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这七个字的千古伤逝之叹,如此不同凡响,直击人心。我想,此刻依然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王徽之感叹的,并不是与一个自己亲近的人离别之痛,而是“人琴俱亡”——琴声如诉,曾经多少美好的回忆,多少高妙的瞬间,都随着琴声的走调琴弦的错乱而蒙上灰尘。伴随着子敬生命始终,本是兄弟两人共同经营的艺术世界已经永不可得。那里风淡云轻,没有任何世俗拘束,也没有乱世中无可避免的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却只有清风朗月、琴曲诗书、兰馨玉质、雪落无痕;那是两人用多年的情感与心心相惜在乱世中撑起来的,那一点点可以让彼此喘息的空间,只能容纳彼此的存在,只有他们共同才能抵达……
所以,在猜到子敬死讯时,他毫不伤悲、在看到子敬灵堂时,他没有眼泪。只有当他意识到,琴声不再,琴弦也随着子敬的死去而都不再调和,生性什么也不在乎,什么都无所谓的王徽之,才终于真正彻悟,随着个体生命而去的,是这个世界一切美好的烟消云散,这寄托自己一生追求的美好,原来如此脆弱!于是悲从中来,那压抑的巨大痛楚,让他“恸绝良久”,只过了月余,也随弟弟而去。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徐亦卒。
——《世说新语·伤逝第十七之十六》
人不免会感到孤独,尤其是在很深的夜晚。
分裂混乱的大时代,日趋逼近的焦虑和迷惑,甚嚣尘上的声音吵闹却没有一个可听……越是纷繁复杂的大环境,个人感受越是逼仄压抑,而越是才情出众,往往也是知觉越为敏锐,也就往往能听到更多别人无法听到的杂音,看到更多隐藏在或纷乱或平静之下异样的预示,从而也会有更多无可排遣的寂寞与痛苦。
这个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的期待一个人,一个人,能和我们听到一样的琴声,能和我们看到同样的风景,能和我们感知到同样的痛楚。
当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人,我们的心,就会变得非常柔软。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尤其在乱世,得一知己,更可遇而不可求。
如果遇到,不知何等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