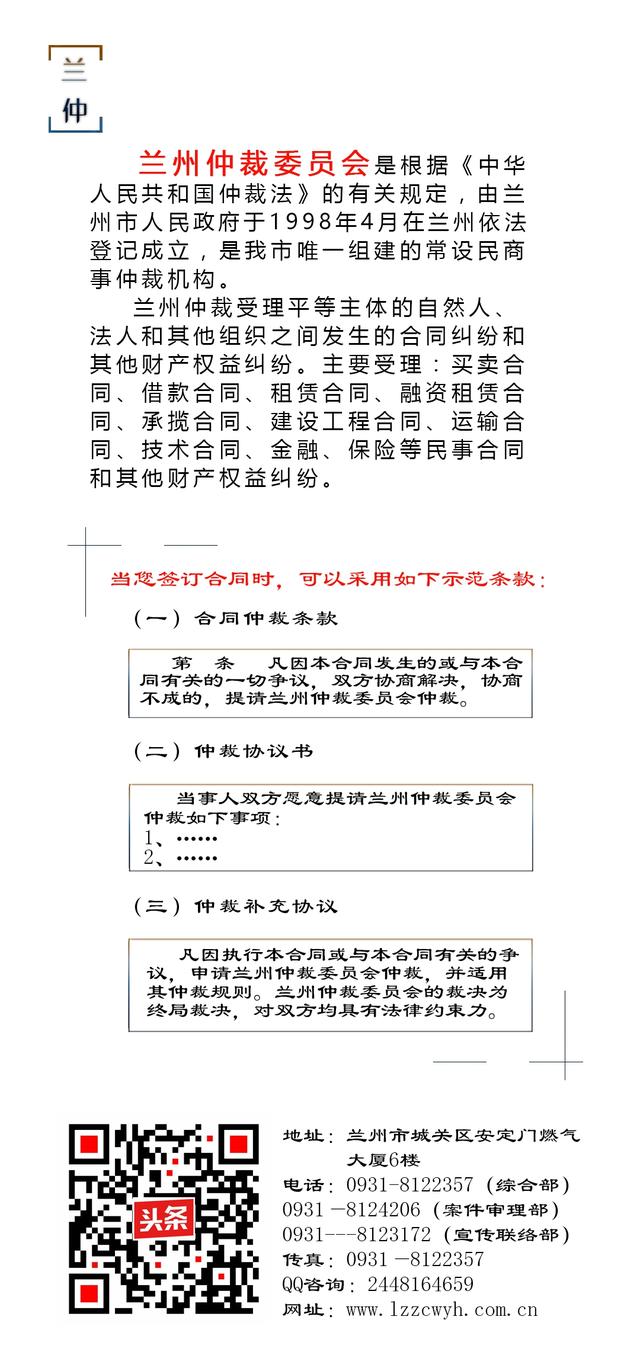本故事已由作者:塔克风,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深夜奇谭”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首先,是你姐姐最近新找回的记忆,回到塔镇几次,旧风景旧物件都不同程度地刺激了她的大脑。”看顾子豪他还是没有坦白的意思,闫荣坤感到遗憾,便自己开始说——
“你要知道,她想起了刘长春不是真凶。在当晚事情发生前,刘长春尾随她,还跟上来说了些话,这给你姐姐造成了震骇,两人蛮力拉扯起来,最后……顾欣,你姐姐不慎把人家推进河里溺死了。她这算自首,在公诉开庭前,我们必要先拘留下她。”
“呃……原来是这样……”
“至于刘长春临死前和顾欣说的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怎么知道?”
“哦,好吧。”闫荣坤也觉得这问题问得有点傻,耸耸肩继续,“刘长春说自己是她的爸爸——他说,你们的妈妈姚美琴,是他从前的爱人,而顾欣就是他和姚美琴的女儿。他那段时间尾随你姐姐顾欣,不是因为想要伤害她,相反,他想保护她,免受那真正黑手的侵害……”
“什么!!”听到那刘长春竟是姐姐的生父,顾子豪震骇不已——“他在胡说八道吧!”
“你真都不知道?”汤国林狐疑的反问道。闫荣坤不懂汤队是真想问这个问题,还是无意义地要激怒顾子豪生气,他也好再——
“我他妈当然不——”
他再猛拍桌子,闫荣坤只觉得耳朵爆炸。估计被问话的人会更不好受吧?
“继续,荣坤。”
“呃好,好,刘长春说顾欣是他的女儿,那几次尾随都是想要保护她——在两起案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应是要履行那么些责任的。就是这样。
“然后,针对你姐这新回来的记忆,我们进行了回溯调查……”
这正是闫荣坤带队负责的部分:关于“刘长春”,秦大哥也说过,让他们“好好去查”这个部分。
经过两天的不懈努力,他们调查了解到:刘长春在正当得意的时候,可谓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虽说没有明面上的丑闻,却有几些业内知情人向他们透露,大作家刘长春,私人关系有些混乱,已经是大家公知又不会去提的“秘密”了。
就目前的信息来看,刘长春直到败诉疯掉,起码交往过7个女人。7个有名有姓被他们追溯到的女人。顾欣和顾子豪的妈妈姚美琴,也是其中之一。
83年11月10日,刘长春的新作活动,姚美琴慕名去参加了。如果顾欣于“日记缺页”发散开的推理没错,那天,刘长春搭讪了姚美琴。
换句话说,姚美琴,就是往后一年多刘大作家的情人。这人勾引有夫之妇是有先例的,几次三番,若是搁在如今,信息爆炸的时代,肯定是要被网友挖出来,谴责到永无宁日。
闫荣坤觉得,他们就好像“网线”,把刘长春的“风流生涯”从尘封的时间里抽解出来。
姚美琴,是刘长春已知的第四名“情人”。在短暂的风花雪月后,86年到87年,刘长春又联系到她,那段时间,闫荣坤甚至还在一家老牌酒店查到两人的酒店记录。
虽然没有实质证据,但结合那日记本里夹着的张律师名片,顾欣顾子豪的妈妈姚美琴,极可能是当年替刘长春还上律师费的女人。
——“你的重点是什么?”顾子豪受不了了,“为什么要一直一直说那个臭疯子的旧事?他跟我妈好过,我姐姐不是我爸生的,好,好,那就算这样子,又——”
“你是几几年生人?”汤队直接发问。顾子豪愣了下。
“回答啊,你是几几年生的?嗯?”
“88年。”答毕,顾子豪的脸像是电壶里的蒸馏水,咕嘟咕嘟,逐渐“沸腾”起来:
“难、难道,你们的意思是……”
“你才是刘长春的儿子,子豪。他大概是脑子坏掉,记错了。我们昨天用你家里的旧牙刷,和当年的样本比对了。”
汤国林耸肩,“结果是你和刘长春铁定有血缘关系。所以,这就是你在犯案之后,DNA证据却指向他的原因。”
砰!
——真相被摆上台面,发出它出场一惯沉重的巨响。
2
忘了具体的年份,反正是很小的时候,顾子豪偷了姐姐顾欣刚穿过的内裤。
他从洗衣篓里挖出来,偷摸藏匿了很久,直到有一天突然觉得恶心,就顺手到外头扔了。第二天,他又为此深切后起悔来。在“行窃”那天往前,子豪甚至搞不清楚那“吸引自己”的是什么,而直到后来才彻底知晓那其中的原委……
顾欣对他很好,他也很喜欢她。但不知怎么,子豪就感觉和她有一种“距离感”,好像她一半是自己姐姐,另一半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存在。这让他很不自在。有时候顾欣抱他,他感觉是关于亲情的,当然是。但有时候,他会被拥抱搞得心神不宁。
这是一种病。顾子豪知道,因为周围没有人是这个样子的。
他无法跟任何人说这些,也不知该怎么消除这一倾向。一段时间,顾子豪觉得自己要疯了。
01年,这种倾向消失了。7月5日晚,他在万店街的弄堂口,找到参加毕业晚会,傍晚仍未归家的顾欣,躺在光秃的水泥路面上,眼睛闭着,呼吸急促——
妈妈让他出门寻她的。那一刻,顾子豪只听自己脑中什么断掉的声音。他犯下了不可磨灭的错误。
3
11年,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顾子豪结识了一叫徐媛清的女孩。
女孩像灿烂的阳光一样,照进他内心的角角落落。
对于自己收获了爱情这回事,顾子豪可谓是五味杂陈:犹记得,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做出了禽兽般穷凶极恶之事。之后呢,一切就像是漏掉的气球——欲望消失了,一夜之间归为零。
类似那些人们常挂在嘴边的“物极必反”之典故,顾子豪开始对此“厌恶”。走在街上,看到有女人穿着膝盖往上的裙子,他都感到难受,想要躲开目光,甚至有拔腿就跑,跑得越远越好的冲动。
当然,徐媛清除外。她穿什么他都喜欢。这女孩习惯性地穿着朴素,经常一身配套的运动服出现在那里,跟自己约会的时候,也不会有多花哨。
这让顾子豪心安,退一步讲,他认为不管徐媛清怎么样,自己都可以欣然接受。因为他爱她。这超越了简单的本能。
顾子豪始终认为,自己余生的安逸,都是碰着“大运”捡来的。他不配拥有这些:大学生活啊,徐媛清,妈妈,还有不知情、依旧对自己很好的顾欣……
01年7月6日早上,他跟妈妈待在病房里陪姐姐。顾欣直到中午才醒来。大家说姐姐是被在巷弄口下了药,十有八九,跟前两起事件的真凶为同一人。同款的药物,这足够说明一切,至于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说姐姐会丧失生育能力……
顾子豪脸色苍白地坐在妈妈旁边,等着顾欣醒过来。
或许她知道是自己干的,睁眼便告发他。又或许警方查出了真相,刚刚来看过情况的毛警官,马上接到电话,折回来把自己给拷走……真的,怎么样都行,他只想要这一切快点结束。自己是说不出口的,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
只是说不出口而已。他急迫地想要别人问他,或是直接查出真相——这样也是一种解脱。
肯定是前面两起案件的凶手——顾欣快要醒的时候,他在妈妈身后哆嗦着思考:那凶手本来打算伤害姐姐的,下完药后,却不知为何就把人丢在原地跑了……我该恨那个人吗?很多年,子豪都在自问:还是光恨自己就行了?
正在他这么想的时候,刚走开的毛大谦警队又蹬蹬蹬折了回来。他一脸严肃地站到病床前,像是酝酿要说什么事似地。来了。见对方就要开口,顾子豪闭上眼睛,感觉异常平静:
“凶手找到了,是……”
是我,是我。他喃喃着嘴型。
“——是一个流浪汉,叫刘长春,桥下面那个人,你们知道他吗?”
!?
那个疯了的作家……
顾子豪不知警方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看样子,刘长春是前面两起案件的真凶。这次也是他给顾欣下药的。真正下手的是顾子豪——然而,大家似乎都想当然地把所有罪名扣到了刘长春头上了。
冲动犯案后他躲在家害怕发抖,证据却指向一个流浪汉是凶手
那家伙死了,听说是莫名落水。子豪眼看事情发展,听着所有人对那刘长春的谴责与咒骂,他逐渐意识到自己这是逃过了?没有刻意去采取什么措施,就这么简单地逃过了?
之后十来年,顾子豪都在拼命地恨自己。不论这种“自恨”有多隽永,他还是无法控制地同徐媛清投入爱河。
有那么一段时间,在徐媛清的感化下,他都开始觉得自己理应享受生活,跟其他并无原罪的同龄人一样。
和徐媛清确立关系一年多,11年中,顾欣也吃药控制住抑郁症。抑郁是当年的梦魇诱发的。这么多年,顾子豪看着她痛苦,身体像气球似地窜上去,自己心里也是煎熬。顾欣有医生配的治疗药,他什么也没有,只能活该地被那“自恨”给淹没。
11年,顾欣病情有了显著的缓解,似乎笼罩在他们头上的梦魇会躲远些了。同时,和徐媛清的关系也让子豪心气大振。他差点就要忽略过去,让人生好歹进入正轨了——那年,又异常悲哀地,他发现自己的身体障碍。这让徐媛清错愕又扫兴,也不明白原委、也不好嗔怪什么。但他自己却知道原因。旧日梦魇从没放过姐姐,当然也从没放得了他。
万幸的是,徐媛清对他表示理解。
16年,也是同徐媛清正式同居的第二年,顾子豪在快乐港KTV会所打了人。他没跟小清,姐姐或妈妈任何人说起这事。被打的是一位朋友,名叫王平,他的大学同学,也是天生的玩乐派。
朋友聚会,唱歌喝酒,当最后离场得只剩两人,他便跟自己说起,关于这里有一种厉害的药在卖。服用后,会叫人昏迷很长一段时间,醒来后也全然不记得之前发生过的事。最重要的,是药本身并不会带给身体带来损害……
半箱啤酒下肚,王平嘴巴肆无忌惮起来,坦言自己用过:他绘声绘色跟顾子豪描述人吃过后身体上反应的种种“症状”:通红的脸腮,无意识却急促的呼吸——“哈哈,你知道吗?子豪……”
顾子豪没有跟着笑。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更何况,顾子豪感觉这些描绘“似曾相识”,像是块血淋淋的磁铁负极,跟自己心底隐秘罪恶的正极撞到一起,震得他心脏嗡嗡巨响……
“这药什么时候有的?”他问。对方误以为是他感兴趣,连忙熟知地解释道:“很早就有,大概00年左右吧?嗯……阿豪啊,要不什么时候我们——”
然后王平就被打了。打得很惨。直到今天,他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就前两天,一个姓闫的警官上门找他,问起他在KTV被打的事。这可教他吓坏了,当着妻儿的面,还算冷静地敷衍过去。
当初,他也是害怕顾子豪跟警方揭发自己的“酒后真言”,才过分宽容地大事化小,把人速速弄了出来。子豪没跟谁提及那些对话,即使他当时真的很……震怒?
不管怎么说,王平悬崖勒马,庆幸自己没有挨揍后还落得被抓的下场——他不止玩过一个女人,在各式各样的场所。这被扒出来还得了吗?幸好幸好……
没想到,从拘留所出来,顾子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自己道歉——说打他是“不应该的”,确实是“酒喝多了”,还感谢他的“既往不咎”。对此,王平受宠若惊。
“你在谁那儿拿药的啊?”说着,顾子豪舔舔嘴唇,有些刻意地坏笑道:“也给我介绍介绍呗!”
4
通过王平,顾子豪结识了那群狐朋狗友,他们一起厮混,喝酒,唱歌,夜不归宿。
那段时间……闫荣坤兀自想——应该就是徐媛清说的“莫名香水味”时期。
当然,顾子豪搭上他们,并非是为了“厮混”而“厮混”:和他们混在一起,他得以慢慢接触到药的销售链,那些是元老的核心人员。他想搞清01年7月5日,那晚真真正正的黑手是谁——因为倘若王平的所言极是,当时那药只在熟人之间交易,不会随便卖给谁……反观刘长春,疯掉已经有八九年,以徐志邦为首的那些家伙又怎会赋予这样一疯流浪汉信任呢?
顾子豪愈发怀疑刘长春是被栽赃的。毕竟,他坠河溺亡这事本身就蹊跷。如果说是被灭口的,他们把他推下河去,为了更好地诬陷栽赃,也就能够说得通——
真凶另有其人吗……
讲到这里,顾子豪这么跟闫荣坤说——一想到那人或许还很好活着,他本应感到愤怒或难过,但是他没有——
“其实我还很高兴,警官……”
他变得干劲十足,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可以分摊自己犯下的罪孽,感觉就没有那么难受了。再去尝试追查其身份,在进行的过程里,甚至能够短暂地、把余下来的罪恶感也一并给屏蔽掉。
在发现陈宏的存在后,所有“七拐八拐”的情绪想法,就全都化成了“愤怒”,化成了怒火:他想要亲手干掉他,既算是赎罪,也是复仇。
是啊,如果没有前面的“两个半”暴行,自己和顾欣的人生也不会转折得如此悲戚。
——“所以,你怎么确定是他的?”
“我错了,搞错了,其实是你们说的那个牛——”
“对对,我就问你,怎么确定是他的。”汤国林打断再问。
“哎,就是……”
他讲的很简单,其实是十分冗长复杂的经过,但为了让两人直观听懂,他尝试着简约——“就是我在欢乐港跟那些人混的时候,知道了徐志邦的存在,他干的事啊,勾当什么的。然后又听说了这人的表哥,和我是一个镇的老乡……”
“陈宏……”
“是的,闫警官,一听到这,我就肯定是他了。”
其实并不然,但对当时的顾子豪来说,这一关联是不能再明确了。况且,他被自己摧残至今,急需一个具象的人来转移怨仇。就这样,他极度憎恨起陈宏来——陈宏,塔镇公交司机,和妻女住在镇上富源路万店街口的小区。
那里就是事情发生的地方,顾子豪没想到“真凶不太会在自家门口作案”这一层,只觉得关联“更大”了,进而无比确定。确定这家伙,就是那诬陷刘长春,害了他们,并逃脱的人。
另一边,顾子豪找机会退出了王平的交际圈子。和那些人一刀两断,他同徐媛清的关系也缓和许多。但因为各种无法言说的原因,他无法开口求婚。小清可是等不及了的。
等不及,以至于在去年年底,就像煽情故事演的那样,自己去买了一颗戒指,希望他可以向自己求婚。
真教人感动。顾子豪看着戒指,和自己心爱的女人,除了同意,不奈他无法做出别的选择。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若要倾身投入新生活,陈宏必须死。他要亲手杀了他。
这风险很大,会断送一切,但若不这么做,他感觉自己也做不好别的任何事情。
报警吗?自首加举报,让警方逮捕陈宏,自己也连带受到制裁……
要不是小清的求婚,子豪或许就会这么做。但他第二怕的,就是让这个女人发现自己的真面目。他不想伤害她,又必须要让那该死的司机付出代价。
思来想去,还是要亲手去做。杀人计划很早便已拟好,但却迟迟下不了手,怕失手后断送一切,也怕得手后加重罪孽。最后拖着拖着,结婚证也领了,婚礼将要在市区塔镇相继举行。
“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顾子豪这么想:必要在婚礼前了却此事——所以,那天晚上,他以“去见一没参加婚礼的朋友”为借口,驱车来到那巷弄口,也是陈宏家的公寓楼下。
他不应该开车来的,因为这就是他的车,案发后一下便会暴露了——面对闫荣坤的质疑,他点点头答:“是,那时候整个人都傻掉了,计划什么的,全都想不起来,脑子里除了要杀他之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就这样,他们跟随讲述,回到唤醒这整件事的源头:顾子豪,在自己的婚礼刚刚结束,就驱车直到一“陌生人”家楼下,上楼敲门,挥刀就捅,再暴力地讲人推搡下楼……戏谑的部分,是他姐姐顾欣,正好就在楼下目击了一切。
“我虽然杀错人了。”最后,顾子豪说,“但陈宏也该死的,该死的玩意儿,不是吗?他算是牛、那个什么牛家伟的共犯啊!”
闫荣坤没有说话,因为怎么回都不是很好。汤队清清嗓子:“省省吧你。”说罢,就摆着那一贯阴沉的脸出去了。闫荣坤没马上去跟:
“谢谢,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
“我罪该万死,是不是?”对方哭着问。
“……”
“能不告诉小清这些吗,我不想,不,不想……”
“对不起,这不是我个人能做主的事情。”汤队后外面催他,闫荣坤沉住气,握住顾子豪的手说,“徐女士可以经受住这些的,她很坚强……”
“我知道,她坚强。可……可她会在我死掉后厌恶我!”
“厌恶”一词的语调很重,像是顾子豪对自己歇斯底里的惩罚。
原本,闫荣坤像憋出些进一步的安慰话,什么“她不会厌恶你的”“要相信你们之间的感情”云云,但都不靠谱,这根本不是他闫荣坤能够保证的事情。
“对不起,对不起。”说罢,他松开手,不再看顾子豪的表情,逃也似地离开这个房间。
5
在案件被警队彻底告破当天,闫荣坤随汤队从拘留所回来,另一边,秦悦民也拆绑带出院了。他还算不上痊愈,只是不用住院24小时观察了罢。
闫荣坤听说了秦大哥出院的消息,打算下班后去他家里看看。
“小金!”在他们的警员食堂,年轻的金凯警员正拎着一袋花卷出来。闫荣坤也不急吃饭了,匆匆迎上去。
“哥?有什么事啊?”
“啊不,没什么要紧的。”他笑笑,“就是汤队让我看到你或老徐,就问问你们调查的进度——怎么样,找到直接证据了吗?证明顾欣致使那个刘长春溺亡?”
“咦?”小金木讷地看他,“我以为徐大哥已经跟汤队汇报过了。”
“有吗?哈哈,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
小金并无参透什么地耸耸肩:“什么也没找到,这么久远的事,前两天我们问遍了所有龙兴港就近住的人,没有潜在目击者。就算真有谁说他看到了,那又怎么证明他的话是真的?这太玄了,昨晚徐大哥就要跟队长说,这根本不可能。”
“这样啊……这花卷挺好嘛!”
“嘿嘿,是啊,我昨天就订了,你要吗,我分你一半?”
“不用了,谢谢!”
临下班前,闫荣坤又在男厕所抓住老徐,问起顾欣和刘长春的事……
“就像小金说的啊,这能查出来我还用在这干活?”
“呃,那你跟汤队说不要查了,他怎么回答你的?”
老徐一副“别提了”的表情:
“汤国林说我们还得查,想办法,最好是找出点什么,间接证据也……反正是什么都可以。”
“这么固执的吗?”
“是。”老徐挠挠下巴的碎胡渣,“他的意思,就像上次研讨会说的:顾欣推刘长春下河,算是我们整个调查链的前提,或者说‘重点’,如果这最后只是顾欣单方面说辞,她说她把刘长春推下河溺死,还是个莫名其妙飞回脑子的记忆?也就是,她甚至自己也没法说定,不是吗?这样在公诉的时候,是不会判那女人有罪的。因为缺乏证据。”
闫荣坤直呼那就这样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判顾欣有罪才甘心呢?
“不,不,汤队意思,他怕法院会认为我们的调查不够牢靠。要尽可能证明顾欣是真的害死了刘长春才行。”
“这有什么关系?!牛家伟的认罪、顾子豪的认罪、还有我们林林总总的周边信息,还会有什么不明确的吗?”闫荣坤哭笑不得。
“我也觉得。”老徐哼了声,“汤国林执拗得要死。那女人已经够惨的了,真他妈——”
闫荣坤点点头——很明显,汤国林这是做给秦悦民看的,当然,他知道秦悦民背着警队开始私人调查,和当事人顾欣有了那么点交情……
以前,秦悦民在队里的时候,两人是一直在“各种吵”的。所以汤国林依旧为秦悦民被停职查看而幸灾乐祸,现在看样子是回不来了,闫荣坤想,大概也是他在其中作梗的缘故。
如果有谁说他们汤队的心眼小,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岂止“小”,是“很小”,小到了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地步……
6
晚上,闫荣坤拜访秦大哥家,跟他讲了现在的情况:
“汤国林又有点发神经了。”秦悦民总结,“因为我的缘故?”
“不过,似乎也并没用。”闫荣坤说,“老徐和小金没那么大能耐,他们找不到证明顾欣所言极是的证据,因为根本就没有。”
“话说回来,汤国林也没有错啊。”秦大哥格局很大地说,“我们是警察。有时候,不免要严谨一点,即使会有些不近人情……”
“……”
“哎,你是警察,我不是咯!”看着秦悦民伸懒腰,闫荣坤缩在那舒适的太妃椅上,两人相对无语了半晌。
“大哥。”闫荣坤找话题,“这个案子,你感觉……”
“我感觉很让人难过。一直是这样。”
“……”
“其实,我跟汤国林想的一样。你们在公诉时候说‘刘长春尾随顾欣,是把她错记为自己的孩子’,还有顾欣声称自己推他下河的事,毫无佐证,那突然回来的记忆,难道真的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吗?”
“你说得对,”闫荣坤点头,“目前来看,无法裁定01年翻案的调查结果。虽然有牛家伟和顾子豪的证词,却没有更直接的东西证明,而且就算他们都没说错,刘长春溺亡的真相也仍然是谜。”
“我觉得是可以裁定的。毕竟两个人认罪的证词摆在那里——”
“但这两段证词其实……也没有实证的……”
“呃,也是诶?”秦悦民费力地想了一会儿,“但顾子豪又杀了陈宏,牛家伟又杀了张孟奇。他们没跑是没跑了……”
闫荣坤点头:“所以我说,这种证据缺失唯一的结果,就是裁定不了顾欣有罪。我们确实不能肯定是她推刘长春下河的。即便真是的话,她也没有恶意,就是一场意外啊!你想想……”
秦悦民又提到,顾欣后面因为过度害怕,在陈宏家楼下吃‘老鼠药’的情节,可以跟牛家伟“把药中转在捕鼠屋”的口供吻合……
“可是——”
他们无谓地讨论了好久。晚上回到自己家,闫荣坤直接碰上床睡着了。他很累,非常累。在梦里,他梦见徐媛清,和她脸上那银线般的伤痕……
7
他们一起在法院外面等我。这让我很感动。毕竟,理论上讲,在这颗星球上,我已经是孤家寡人了,也会一直这么孤寡下去。
他们有四个人,分别是小清,闫警官,秦大哥,和一个精干的短发女,貌似是秦大哥的妻子。
“我觉得就是我。”碰上他们,不知该先说什么,就无解地冒出这么一句。
“姐,你别说这个啦!”小清笑,脸颊上那道划痕随光线的角度若隐若现。她像是毫不在意,所以也没显得别扭。
因为不能逗留在法院大门口,我试着迈开步子,大家也都紧紧地跟上来了。此时此刻,真正意义上地,一股暖流包围了我。
“这两月受苦了,顾女士。”秦大哥开口。
“没有……”
“有人欺负你吗?”小清问。
“哈哈,其实没那么可怕。”闫警官笑。我这才发现他和小清挨得特别近——“你们两个……”
“啊,他俩成了。”秦大哥响亮地说,闫警官一副被阴了的尴尬表情。小清则是抿着笑低下头去:
“所以,姐,没人欺负你?”不知是不是转移话题,她又问。
“当然没有——所以你俩是什么时候……”
一路说,走到对街不远的一家饮料店里。我暂且麻痹在徐媛清和闫荣坤的爱情故事里,但那自身空虚的惶恐逐渐反应上来。
我爸妈死了。
弟弟也即将被判死刑。
那还不是我亲弟弟。对此,我真的没法思考什么——就像一场极端的噩梦,太太可怕了!
“别哭啊,姐。”看我在哭,小清绕到桌子这边拍我。然后我们俩都难受地哭了出来,抱在一起,像是一对落难的姐妹。
“对了对了,顾女士?顾欣?”秦大哥的妻子开口唤我,“听说你有写作?在……前一段时间?”
我鼻子抽不停,有些狼狈地回答说是的。在拘留所,我有用纸笔间断地写东西:不想逃避,就逞强地想把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写下来……
“能给我看一眼吗?”
“呃……”
“钱澜是出版社的编辑,”秦大哥介绍道,“你起码可以相信她专业的阅读态度。”
我还是不想交出稿子。钱澜女士理解地点头,转而问:“所以只是简单的记录吗?把发生的一切给书写下来?”
“差不多吧?也不清楚,就是冲动就写了?”
直写到这里,我依然记得钱澜女士当时的话:
“这是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她说得诚恳,“请原谅我用商业的眼光看待啊——这种当事人的切身经历、也就是正发生的事件,一贯是非常具有卖点的……”
“可我不想把自己的事都抖出去给人看!”
“这是一个收入来源,至少在你寻到下一个工作往前,可以凭借我们的稿费生活。”
是的,我被公司辞退了。这很正常,我接受的可是“杀人与否”的庭审。
“保证有稿费?”
“发布了就有,在我们合作的一些网站上。而且我估计啊,看得人不会少,收入也不会低。”
——“你完全可以不听她的。”秦大哥认真地说。
——“对啊,姐,你又不是没有积蓄,不是吗?”徐媛清也说。我恍然意识到,倘若我写下这一切发表,发生过一切美好的不堪的,全都会狠狠地公之于众。
“是的,抱歉,我不想发布。”我话音刚落,钱澜略失望地撇了撇嘴,另外三人则都是“舒了一口气”的表情。
8
——“你还是不想回来?”
——“不,荣坤,别再说了。”
一个月前,闫荣坤联合小金,扒出了一桩舞弊丑闻。是关于汤国林的。简单来说,大半年前,上级已经获批通过了秦悦民的复职,委托汤国林加以转告。
他确实转告了,说秦悦民“又没通过,估计是没戏了。”
这让秦悦民受伤不已,为了生计,也去寻了其他工作。最后,姓汤的再转而对上面说:秦悦民找新工作了,不要回来……
就这样,乍一听都有些魔幻——汤国林以极快的速度安顿好一切,添油加醋地丑化秦悦民,搞得他们连最基本的通知讯息也没发出,就这么默认他不想复职了。
至于闫荣坤是如何发现,在顾欣的这件案子接近尾声之际,小金偶然听得几位领导谈论秦悦民,关于他擅自调查并找上牛家伟的事:自己不想当警察,还尽逞英雄?
小金把这跟闫荣坤说了。听罢,闫荣坤愈发感觉不对,就鼓起勇气找局长问,最后竟挖了这般惊天秘密……
秦悦民初听到这一切,气得摔碎了杯子:“这小子怎么敢——”
几位领导在得知真相后,先找到了汤国林咨询情况。就在当天,他们就接到汤队被撤职的消息——“是否开除和新职位暂定……”
闫荣坤也不大懂其中的原委:据说在办公室,汤国林死不承认,最后竟情绪失控,当场吵了起来……
“不是,他到底和秦悦民有什么梁子啊?”小金无知地问。
“一直看不顺眼的。”闫荣坤叹气,“其实我也不是太清楚。
就这样,汤国林无谓断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另一边,熟悉的上司重新对自己抛来了橄榄枝,秦悦民却开始犹豫了……
他拒绝了归队的邀请。
——“你是我们中间最好的。”在法院接完顾欣,送秦大哥回去的车上,闫荣坤又开始劝。
“你也不差。老徐,小金,你们全都不差——这么大的部门,不缺我一个的,荣坤。”
“……”
“去年……”他们的车倒出法院的停车场,来到街上,饮料店门口的三位女士朝他们招手。闫荣坤回礼。
秦悦民自顾自往下说,“去年啊,我觉得我命实在是很大,能够挺过来。然后你看现在,单单一老头牛家伟,就差点把我给杀了。我不是觉得不值,就是……哎呀,怎么说,总感觉,是时候退出了?”
“你离退休还有十年呢!”
“是啊,我50岁了。”秦悦民耸肩,“但事不过三,何况为了家人,我也不愿再去涉险了。”
“……”
“……”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闫荣坤另起话头。
“什么?”
他把车子安稳停在一处红灯前,组织了一通语言:“那个,我当上大队长这事儿,你有没有……就是,推波助澜?”
“有。”回答十分干脆。
“有啊?”
“是的,有。”秦悦民得意地笑,一副“你小子终于问了”的表情,“张局他们叫我回去,可能是想弥补我吧?或是怕我会不满,把汤国林干的事到处去说,搞得形象不好。本来,没那个姓汤的搅局,我顶多还是个副队。现在好了。但是、但是我不想回去了你懂吧,就顺便……引荐了一下你。”
“这样啊……”
“说来说去,我仅仅是辅助作用。”秦悦民看着指示灯变绿,惬意地闭上眼睛,“你用降服了牛家伟,救下徐媛清和顾欣,在整个案子的推进里面,全程也是功不可没的,我提到你,只是让你上去得更加确定而已。你很优秀,荣坤,比我们都优秀,不是现在,早晚也会独当一面的。”
“呃,怎么有点、有点感动啊哈哈!”
“感动吧!”秦悦民跟着大笑,“好了,就是这栋楼,就是这里。”
“你就在这楼里做安保啊……”
“对,比较清闲的,挺好。”
“嗯……慢点哈!”
“拜,以后来找我的话,别带什么案子了懂?”
“那我带什么?”秦悦民半身踏出车厢,闫荣坤抖机灵地反问。
“带……呃——”他特意想了想,似乎是要憋出什么幽默风趣的答案,“带、带脑子!”
可惜,有点牵强、不好笑。闫荣坤再次说拜后,秦悦民关上车门,发出“咚”的一声,干脆铿锵,就像这位饱经风霜的奔五大叔,他二十多年“断案生涯”的缩影——
9
(尾声)
虽然弟弟的身份特殊,但我还是把他和爸妈葬在了一起。
一切都过去了,对于这无情残忍的真相,我也试着开始坦然。
对着三人的墓,我压抑地哭了好久。这到底算是什么呢?
墓地在塔镇以南的远郊。搭公车回家的路上,又经塔镇,我有些木然地看着种种一切:曾经热闹的街巷,大多店铺都成闲置了,几些不温不火的赔本小店夹杂其中。就像一盆养了很久的植物,在七成旧的败叶之间,三成新枝勉强坚硬地开放着。
龙兴港桥,一辆韵达快递的面包车停在下面,快递员被围在快递箱中间,拿手机艰难跟谁解释着什么。
我搭的公车开上桥,下桥右拐,很快掠过弟弟婚礼的酒店,再拐弯,就朝市区的方向去了。
塔镇……
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回来。
晚上,在格外孤寂的公寓房间里,我心血来潮地研究起相亲网站,兴奋而忐忑地注册下自己的名字——“顾欣,女,39周岁”……
最后只是存了草稿而已。我还是没有信心,一直折腾到半夜十点,一阵钻心的难过迎面袭来,我发抖哭着关电脑,也没有洗漱地躺下了。
失眠,失眠,失眠。凌晨三点,我下定决心地下床来,光着脚跑到浴室里,打开那有些跳光的白灯,对着镜子屏息站定:
我看到一张不好看的大饼脸,一张受伤的、憔悴——甚至已经开始显老的脸。
这就是我吗?
我没有往下去想这问题的答案,深深深呼吸,随即,做出第一下的尝试……微笑。
没有成功。那就再来一次。
第三次……
第四次……
再来一次……
到第九次,苗头开始有了。我试着加以“调整”,调整咧嘴的弧度,让肌肉尽可能放松、放松、放松……
最后,我找回了爸爸留给我的笑容。
很快。
并没想象中的困难。
我对着镜子笑,忍着不争气的泪珠,笑到脸颊发僵为止。实在没力气了,就关灯,摸黑回床躺下。
找回一件丢失整20年的东西,没有掐表,大概也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是啊,真不难。
我想,对于一个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人来说,只要有心,总归是能寻回“三两旧物”的。然后,我就可以带着这些失而复得的东西,在某个全然准备好的时刻,踏上崭新路途。
那是旧日梦魇伤不到我的地方。我咽下虽迟但到的睡意,于心中告诉自己——
“未来”。
是的没错。
那地方叫作“未来”……(原标题:《旧日梦魇(四·大结局)》)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