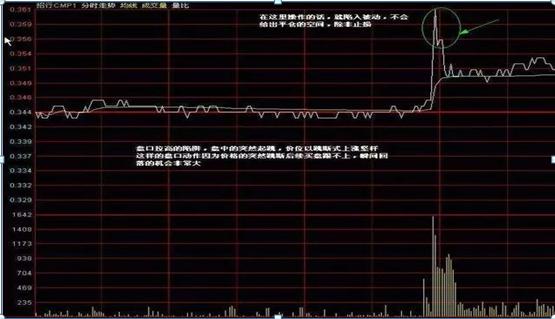二十年前,在《“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中,我写下这么一段话:“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而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之挥洒自如。”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总统黎元洪签署任命状。
不过,国人之谈论蔡元培(1868-1940),多强调其积极进取,而不太涉及其消极退避。其实,阴阳合一,进退有据,乃教育家蔡元培及其执掌下的北京大学在北洋政府时期得以生存发展的关键。谈论这个话题,不妨从蔡元培的不断辞职说起。
遥领北大
八次辞职与两次欧游
1917年7月1日,张勋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两天后,蔡元培发布辞职书。7月20日“得北京大学职教员公函,请回校”,三天后回校复职。
1918年5月21日,因学生对《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多所怀疑,发起抗争,蔡元培再三劝阻无效,向总统发送辞呈,各学长一同辞职。同月23日,因总统挽留及北大学生认错,蔡元培等复职。
1919年5月9日,救出被捕学生后,蔡元培当即离京,留下汉代《风俗通》“杀君马者道旁儿”等,让世人猜谜去。此后,学生抗议、教育总长同情、总统挽留,蔡元培则称病故乡,一直到9月20日方才回校复职。此次四个半月的出走,多方博弈,牵涉面甚广,最具代表性,也最有策略意义。
19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要求以现金发薪罢课,蔡元培与各大专校长一起辞职。1920年1月8日,因抗议无效,蔡与各大专校长再次辞职。1月12日,政府答应所有要求,教职员联合会遂发表回复职务宣言。
1917年夏,北京大学文科英文学门第一次毕业合影,前排中坐者为蔡元培。
1922年8月17日,因政府欠薪且侮辱校长,蔡元培领衔,与北京各国立学校校长一同发辞职通电。9月11日,教育经费依旧无着落,蔡刊发与北大脱离关系启事。9月21日,政府拨给两个月费用,答应月底前再给半个月,校长们于是复职。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蔡元培愤而辞职,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以及众多教授也发表启事:“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学生们没想到蔡校长如此强硬,惊骇之余,赶紧认错。10月24日,蔡发致北大辞职教职员信,要求恢复原状。
1923年1月17日,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蔡元培向总统府提出辞职,且立即离京。北大及北京各校师生于是开展驱彭留蔡运动,一直坚持到9月4日彭去职,12月27日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此次动荡才告结束。可此前的7月20日,蔡元培已启程赴欧,且一去不再回北大。
1926年3月18日,蒋梦麟致电蔡元培,告知北大学生惨死三人,重伤十余人,蔡元培对北京政府彻底绝望,6月28日致电国务院及教育部,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北大同仁及学生一如既往,极力挽留,教育部也去电慰留。但这回蔡元培打定主意,不再回北大。校史上说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任期,一直到1927年7月,但那只是“遥领”,即密切关注,而非真正履职。
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第四次毕业摄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钱玄同、蔡元培、陈独秀、黄侃。
此事还余波荡漾,1927年8月起,北大经历了两年反合并、抗改名的斗争。重获新生后,北大师生强烈要求蔡元培返校任校长。1929年9月初,蔡给北大师生复信,表示愿意重回北大,只是需9个月后才能到职。但随后因国民政府取消了校长遥领制度,蔡元培只好再次请辞。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同意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辞职,并任命蒋梦麟为北大校长。
这就说到蔡元培之于北大,其实长期处于遥领状态。1919年四个半月的出走,是五四运动的余波,多为学界关注。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14日的欧美考察,说出来的是调查欧美大学情况、访求教员、筹建扩充北大图书馆,但据蔡元培《自写年谱》,背后原因是张作霖、曹锟对蔡元培这北大校长很不满,“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情况”。至于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而辞职,1923年7月20日开始赴欧研究,1926年2月3日回到上海,但并没回北大,而是滞留东南一带,从事政治及学术活动。这么算下来,蔡元培执掌北大这十年半(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真正在校时间只有一半。
不断辞职
保持理想的特殊形式
作为长期执掌中国最高学府的蔡元培,其不断辞职,给北洋政府很大压力,让其内火中烧而又有苦难言,还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新派人士为此抗争叫好,旧派人物则不这么看。
林纾去世前一年编定《畏庐文钞》(1926年刻本),除选自《畏庐文集》《畏庐续集》《畏庐三集》者外,便是此置于卷首的撰于1923年春的《续辨奸论》。此文没有直接点名,但仔细玩味,其针对的应该是北大校长蔡元培。“鱼朝恩之判国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贾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鲁而不学。”这两个都不算僻典,林纾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大概都能读懂。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左二)与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在北京西山卧佛寺。
以判国子监(国子监最高长官)来影射北京大学校长,这很容易理解;而更贴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年初,蔡元培一直与北京政府抗争,1923年1月17日更是为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愤而辞职,并立即离京。此事引起很大风波,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可谓路人皆知。林纾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政治立场,但嘲笑他没有学问,说其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这明显不入流。因为,按照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及学术标准,这位前清翰林、留学德国多年、曾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的北大校长,无论如何是值得尊敬的。(参见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对于蔡校长的不断辞职,同属新文化人,北大教授胡适与陈独秀的态度有很大差异。1923年1月21日,胡适在《努力周报》第38期上发表《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称此举“确然可以促进全国国民的反省,确然可以电化我们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觉力”。三天后,也就是1月24日,陈独秀在《向导》第17期上发表《评蔡校长宣言》,对其辞职表示不以为然,理由是:“打倒恶浊政治,必须彻头彻尾采用积极苦战恶斗方法,断然不可取消极的高尚洁己态度。”2月4日的《努力周报》第40期上,胡适刊发《蔡元培是消极吗》,针对陈独秀的批评,为蔡先生的以辞职为抗议辩护。胡、陈的分歧,在于辞职这种抗议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在蔡元培的动机。世人即便不认同蔡先生的政治立场,也很少像林纾那样,认为其不断辞职是为了加官晋爵。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图为院长蔡元培(前排左三)与同仁合影。
蔡元培的政治立场及个人趣味,在其辞职说明中,有很明确的表述。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称:“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215-21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这篇激愤的宣言,因堂弟蔡元康的阻止,没有公开发表,但可见他对于官场的厌恶深入骨髓。这里既有政治立场,也含教育理念,还包括喜欢研究学问、讨厌繁文缛节的性格特征。类似的表述,在日后几次辞职书或演说中,都可以看到。除了政治污浊,经费短缺,蔡校长还再三提及个人趣味:“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道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每天腾出一两点钟读读书,竟做不到,实在苦痛极了”(《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这种书生本色,是其多次脱离政坛,赴欧留学或研究的内在动机。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右)与鲁迅、英国作家萧伯纳合影。
蔡元培的辞职,不全然是针对政府,也有关涉学校内部治理的。1922年学生因不愿交讲义费而聚众抗议,历来温文儒雅的蔡校长,居然在红楼门口挥舞拳头,怒目大声说“我跟你们决斗”,并随后带领全校重要教职员集体辞职。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体师生会议上,蔡元培解释他这次为何要“小题大做”:“二千几百人中,偶然有几个神经异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数人有这种异常的计画,为什么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从?为什么其他大多数的人都像隔岸观火?事前既不加纠正,临时又毫无制裁;数千人的社会,其中分子,彼此不相关切如此;将来土崩瓦解的状况,可以预推了。”这里的假设是大学生“知识比常人高,应该有自制的力量”,能独立判断,不受外界蛊惑(参见《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72-275页)。斥责“几个神经异常的人”,表面上是抱怨大学生缺乏自制力,其实是希望借此整顿“五四”后变得松垮的校园秩序。
蒋梦麟日后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中,谈及蔡元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既希望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又十分担忧日后的校园秩序:“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西潮》第127页,香港:世界书局,1971年)。以此担忧,反观1922年的“小题大做”,就是为了给北大学生敲警钟——不能滥用闹学潮的权利。
兼容并包
永远的北大校长
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之值得不断追怀,在于其一举奠定了这所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可与蔡校长比肩者。时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长北大,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载难求,不可复得。
谈论蔡元培的成功,其实,还有一点不能忽视,那便是时代的需求。蔡元培长校北大的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国根基尚未稳固,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军阀混战,教育经费无着,令大学校长极为头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处此新旧转化之际,没有不可逾越的边界,也没有不可挑战的权威,乃“尝试”各种新制度的最佳时刻(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晚年蔡元培
比如,1917年秋北大评议会的设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创举。过去的北大,校长大权独揽,教授们只能被动服从;蔡元培立意改变这一现状,不再是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而是创设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的评议会,除校长与各科学长之外,各科教授自选各本、预科教授二人为评议员,一切重要校政及规章,须交评议会审议通过方能付诸实施。这一制度设计,最初是为了压缩校长权力,发挥教授治校的积极性;可到了危机时刻,另一个功能凸显,那就是即便校长不在,学校也能正常运转。
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决意辞职,为此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其中特别提及当初为防止校长个人去留而影响整个学校的命运,特意在校中设立评议会等各种机构,“完全倚几位教授为中坚,绝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3页)。前面提及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有一半时间不在北京,属于遥领状态,但学校仍能正常运转,与这一基于教授治校理念发展而成的制度设计有关。
蔡元培之所以能长期遥领北大校长,除了制度设计,还与蒋梦麟这一可靠且合适的代理人有关。1919年7月,五四运动及校长辞职风波尚未完全消歇,蔡元培决定暂不回北大,而是委派自己早年学生(绍兴中西学堂)、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研究哲学与教育学、1917年3月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19年初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蒋梦麟作为私人代表,回北大主持校务。而且,蔡元培1920年出国考察,1923年赴欧研究,都是蒋代理北大校长。在主持北大校务期间,蒋梦麟发表众多演说及文章,大都强调北大须加强管理,不能滥用自由高调与罢课手段。
蔡元培与第二任妻子黄仲玉及子女
1923年12月,正代理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特为校庆撰写《北大之精神》,称北大特点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与之密切相关的,便是两个明显的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则个性发达而群治弛。”有鉴于此,必须在“相当范围以内,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第47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张“整饬纪律”,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学生们所不爱听的。可如果没有蒋梦麟的“黑脸”,单靠蔡元培校长的“红脸”,这大学是无法维持下去的。某种意义上,职业教育家蒋梦麟的“务实”,是蔡校长得以“高蹈”的前提。
大学最终如何发展,取决于各方力量的博弈,并不完全体现校长的意志。基于此判断,我认可蒋梦麟的工作,二十年前的断言,今天看来依旧有效:“历任北大校长中,名气最大的当属蔡元培。对于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确实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历史学家笔下,蔡氏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无意中压抑了其它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氏的早年学生蒋梦麟。”(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段话,被日后很多谈论蒋梦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阅读这段话,最好与我对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对照,方不致出现大的误差。蒋梦麟并不具备蔡先生那样的崇高威望,也没有“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优秀的大学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样成为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象征。这就说到了带自嘲性质的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能是北大的“功狗”的论述(参见蒋梦麟《忆孟真》,1950年12月30日《中央日报》,后收入传记文学出版1967年版《新潮》)。既然那么能干,为何世人普遍认定,兢兢业业的蒋梦麟,其历史地位不及蔡元培?关键是对大学精神的理解、阐扬与坚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乃大政方针,影响极为深远。至于蒋梦麟,办事能力极强,人格操守也没有问题,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点,则会发现他太守规矩,缺乏那种开天辟地的气魄——当然,也没有那种机遇。(参见陈平原《作为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书城》2015年第7期)
蔡元培诞生一百二十周年纪念邮票
蔡元培每回针对现实政治的辞职,都是惊天动地的事件,北大师生马上发通告挽留,全国学界随即多有呼应,很快酿成了大大小小的风潮,政府即便很不情愿,也必须出面表示慰留。也有不懂其中奥妙的,如1920年1月18日,风潮已经过去了,代理教育部部务的傅岳棻竟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应接受蔡元培辞职。那本是各大专校长的统一行动,如今枪打出头鸟,专门针对北大校长蔡元培。闻悉此讯,北大学生强烈抗议,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展开质询。1月23日,国务总理只好出面解释,称当时虽有此议题,但“兹事关系颇大,故已搁起”。在政局动荡、学潮频繁、大众传媒十分活跃的年代,守土有责的官员们都懂得,接受蔡元培作为一种政治抗议姿态的辞职,那是很危险的。
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理想性,蒋梦麟则代表了现代中国大学的现实性,二者须互相参照,方能准确阅读与阐释。北洋军阀时期,蔡元培可以借助自己的名望、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政治和军事力量的牵制,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独立。北伐成功,国民党统一中国,开始推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审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参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
可以想象,1930年起正式出长北大十五年的蒋梦麟,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样为坚持自己的学术理念,动辄挂冠而去。将不断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抗争手段,那只能属于蔡元培,蒋梦麟及其他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都没有这个本钱。撰文 | 陈平原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