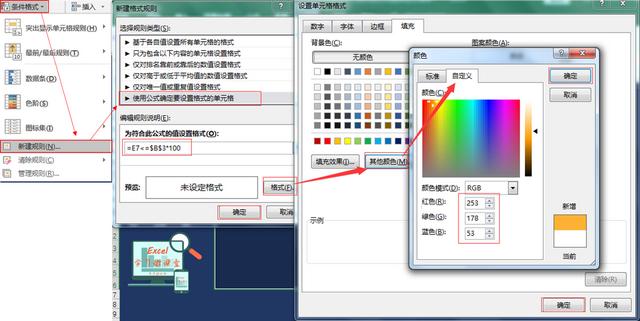作者:Michael Henry
译者:覃天
校对:易二三
来源:Positif(1978年5月刊)
记者:你是怎么开始《爱的亡灵》这个项目的?
大岛渚:这部电影与《感官世界》的联系十分紧密。对一个创作者来说,通过一部新作来回应影评人此前给予他的认同,并且试图超越前作,这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
事实上,在1976年底,也就是我全身心投入到《感官世界》的那一年,一个不知名的人——中村糸子给我寄来了她的书。我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了很多出版物——有人请我审阅的新书,以及不知名作者的未装订手稿。我经常花一整天的时间翻阅它们。但是当我在做一个具体的项目时,我会迫不及待地打开信封,但会过一会儿才去看里面的内容。当我开始写下一部电影的剧本时,我正要把中村糸子的书放在一边,但是它的标题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长塚节:三代人印象中的小说〈土〉》。
《感官世界》
几个月来,我一直把长塚节的小说《土》放在抽屉里,我认为它是一部杰作。而这位不知名的作者在她的包裹里附上了一封信,信中有一句话格外醒目:「我相信《感官世界》的导演一定会明白:即使在日本历史的黑暗时期——明治时代,爱也是存在的。」她补充说:「这本书有很多印刷错误,但如果没有朋友之间慷慨提供的时间,建议和帮助,它永远不会面世。」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即有幸第一个读到了手稿。
记者:中村糸子的手稿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当时正在着手写的剧本?
大岛渚:中村糸子想首先通过写作传达出长塚节的真实形象。她说,「如果我不写,谁会写呢?」当然,她从未见过这位生活在1879年至1915年间的伟大作家,但她的祖父和父亲很了解他。他们向她详细地讲述了许多关于他生活的趣闻轶事。将长冢节和中村三代人联系在一起的故事将构成一个真正的传奇。从这个传奇故事中,长塚节的形象跃然纸上,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天才。你能从中村糸子笔下的长冢节身上感到温暖。
《爱的亡灵》
为了丰富她的传记,中村糸子还提到了人力车夫仪三郎被不幸谋杀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1896年2月20日的晚上,她经常听说这件事,因为她的父亲曾是犯罪现场的警方调查员。根据中村的说法,这位小说家对这起谋杀案非常感兴趣,这起谋杀案发生在离他很近的一个村庄里。他本打算写一部小说,但还没来得及写就去世了。在询问了所有可能知道这起谋杀案的人之后,中村把她所有的发现都收集到了一个故事中。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它确实证明了「即使在日本历史上这段黑暗的时期……爱是存在的。」
我被更深地触动到了,是因为我正在写的剧本的故事,发生地的距离和故事的时间,都和中村提到的事件相近。我的主人公不是一个人力车夫,而是一个在1926年,出现在所有日本报纸的犯罪记录中,绰号叫「食人熊」的马车司机,为了描述贫苦农民对爱情的渴望,我创作了一个与中村非常接近的故事,所以我首先尝试在自己的剧本中加入车夫被谋杀的情节。但随着我的进展,手稿中的人物不断地对我施加影响,直到他们侵入了整个故事。最后,我决定给中村写信,并得到她的同意改编了她的一部分作品。
记者:你认为《爱的亡灵》和《感官世界》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你是在开始这个新项目的时候,还是在执导它的时候,想到了制作一部与《感官世界》对应的影片呢?
大岛渚: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在一片泉水多次沐浴」是十分寻常的。而你提到的这两部电影之间密切的关系似乎确实存在。就像在《感官世界》中一样,《爱的亡灵》的故事讲述的是一男一女毫不犹豫地将他们的日常存在与他们最深层的性冲动结合起来。如今,没有什么比探讨爱情的各种形式更让我感兴趣的了,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爱才能拯救那些人。
《感官世界》
记者:在《感官世界》中,那对情侣自始至终创造了一个如此精致的,纵欲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直到石田吉藏最终自愿性的死亡。而在《爱的亡灵》中,这对夫妇似乎是自己欲望和幻想的牺牲品,而女主人公阿石和丰次之间的激情被描绘成应该下地狱的一种感情。这是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不贞爱情的命运吗?或者你认为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悲剧的命运?
《感官世界》
大岛渚:《感觉世界》中的空间被不同的房间中的爱欲所勾勒出来。它是人工创造的、完全是为了纵欲而设计的。另一方面,在《爱的亡灵》中,这一切都关于自然。阿石有一所房子,她和她的丈夫住在那里。丰次有一间小茅屋,他和他的弟弟住在一起。这两个地方都不是人造的。这对恋人生活在恐惧中,因为他们经常感到大自然的威胁。
我试图描绘人类在原始阶段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部新电影回到了所有生命的根源,比《感官世界》所探讨的要深刻得多。这对情侣似乎因为性欲而被扔进了地狱,但在我看来,大地的隆隆声,风的低语,树木的沙沙声,鸟儿和昆虫的歌声,简而言之,所有的自然之物,都在引导这对夫妇进入地狱。而鬼魂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性和爱情都没有任何意义。生命本身没有意义。如果生命没有意义,那不就是地狱吗?我所能做的就是向你表达和投射这个毫无意义的人间生活,这个「地狱」对我来说永远是美丽的。
记者:你的故事中的超自然因素和日本鬼故事的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大岛渚:在日本的传统艺术中,无论是歌舞伎还是讲谈,都经常提及鬼魂的存在。事实上,这些故事大多来自中国,它们被改造成了具有启发性的复仇故事。我故事中的鬼魂完全不同,他出身于日本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民间传说,他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土生土长的幽灵,很少出现在银幕或舞台上。
对于阿石和丰次来说,就像村里的人一样,他不属于想象中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他,并完全进入这个超自然的宇宙中。不过,我知道今天的观众只有靠想象才能「看见」鬼魂。为了让观众做好准备,我必须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因此,举个例子,我处理肉体性爱场景的方式不能全是露骨直白的。
记者:你将你故事的一部分聚焦在了一口老井上,这是一个从外部到内部的象征性的通道。你有没有觉得它是一个介于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带有象征性的地方?
大岛渚:我在22岁时写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就叫做《来自爱情的深渊》(译者注:大岛渚的第一部编剧作品应为1953年,与川端康成共同编剧的《千羽鹤》,大岛渚提及的可能是次年一个没拍出来的剧本)我们当时都进入到了那口旧井中。当你向井里扔进什么东西时,你可能期待得到回应。这对情侣在影片结束之前来到了井下,这是因为我想表达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还在井底!
记者:你为什么要将丰次的弟弟处理成一个傻子?电影结束时,当「喧哗与骚动」过去后,电影是以这个「傻子」一个人独自在这个被遗弃的村庄的视角结束的吗?
大岛渚:如今,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会认为把这些「白痴」送进精神病院是个好主意。在过去,在日本的所有道路上,你都会遇到他们。自然法则不就是我们应该生活在他们的身边,就像我们生活在动物和鸟类中间一样吗?
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一个「由白痴讲述的故事」。按照日本古代故事的传统,叙述者是一位老妇人。脸上布满深深皱纹的女人。像土地的皱纹一样深,因为土地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记者:当丰次推开她正在哺乳的婴儿时,阿石和丰次之间的恋母情结就非常明显了。在《感官世界》中,你把任何精神分析解读的责任都留给了观众。从那以后你有没有变化和进步?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电影比任何其他导演的电影都更深入地渗透到潜意识中?
大岛渚:我只能重复我一直说的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按照他们看到的方式来解读我的电影。也就是说,我不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去解读世界的人。我认同像阿石和丰次这样的人的存在,认同那些活着然后死去,却无法预知自己命运的人。他们是我觉得最亲近的人。如果你称之为接近「潜意识」,我接受你的表述。然而,我会思考,是否艺术家的作品难以表露和投射到他自我的范围之外,并且那些解释也会尽可能地简单。
记者:阿石的失明代表了什么?这是不是「俄狄浦斯神话」的另一处例子?
大岛渚:这是否会是仪三郎想要对阿石施加的惩罚?或是完整而彻底的爱的表达?如果失明度过一生,我们不是更快乐吗?
记者:当仪三郎的尸体从井里被拉上来时,阿石的眼睛是不是在那一刻似乎又能看见了?
大岛渚:这一观点只引出了一个问题:「阿石的眼睛看到仪三郎了吗?」每位观众都可以自由决定。但在我看来,情况就是这样。
记者:为什么丰次是全村里最后一个「看见」鬼魂的人?
大岛渚:他怎么可能看不到呢?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主啊,您要去哪里?」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也是一个永恒的真理。
记者:代表法律的警长的角色出奇地可笑,你甚至把他打扮成农民。他是来自日本喜剧传统的角色吗?
大岛渚:我经常用带有喜剧感的演员来扮演警官的角色,因为这就是我看待权力的方式。这些权力的代表们越是搞笑,也就越让人可怕。
记者:电影中超自然现象的表现非常简单。你是如何构思和指导这些效果的?
大岛渚: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导演「特效」。你谈到简单,但就像我说的,我的鬼魂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鬼魂,不同于传统装饰艺术经常用于道德目的的幻影。
记者:在影片的摄影风格上,你给予了摄影师一些余地,还是你自己有某种特定风格上的要求?
大岛渚:我要给我的剧组或演员口头指示吗?当我组建我的团队时,我会根据他们自己的风格来选择他们。他们阅读剧本,尽最大努力与故事的要求保持一致。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种和谐,这种统一,不需要我用语言来表达,就能自行解决。我真正想要的是每个人都能在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发挥自己最好的一面。
记者:为何《爱的亡灵》这次增加了与法国的合作?
大岛渚:我并不特别致力于在国际合拍片的框架内工作,但这让我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日本。我与阿纳托·多曼再次联合制作的《爱的亡灵》是我加深对日本的看法的又一次机会,因此也加深了我对世界和男人的看法。
记者:你曾于1969年说,「性和犯罪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人性中最暴力的冲动。」在《爱的亡灵》中,这两种冲动一同贯穿着全片。你会在你未来的作品中延续这种方向吗?
大岛渚:在执导我的第一部电影几年后,我发现我对性和犯罪这两个话题非常感兴趣。随后,我的电影以一种十分具有分析性的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今天,我只是想把性和犯罪赤裸裸的现实呈现到观众的眼中。
记者:一开始,你自己承认,你的目标是「摧毁所有的美学」。然后你找到了自己的美学,你曾经用一个黑色或暗色背景下的火焰为特色的镜头来总结这一美学。人们应该在这张图片中看到消耗你角色的激情的隐喻,还是你自己的创造性努力的隐喻?
大岛渚:自从我的第一部电影——主要是《日本的夜与雾》以来,一些评论家就注意到了这个镜头,一个在黑暗中燃烧的火焰的镜头。对他们来说,这是我作品的特色。对我来说,这团火焰代表了我笔下人物的生命。但它也是我们生活的一幅图景。我经常引用这句格言:「就像居住在深渊中的鱼一样,只有自己发光才能找到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