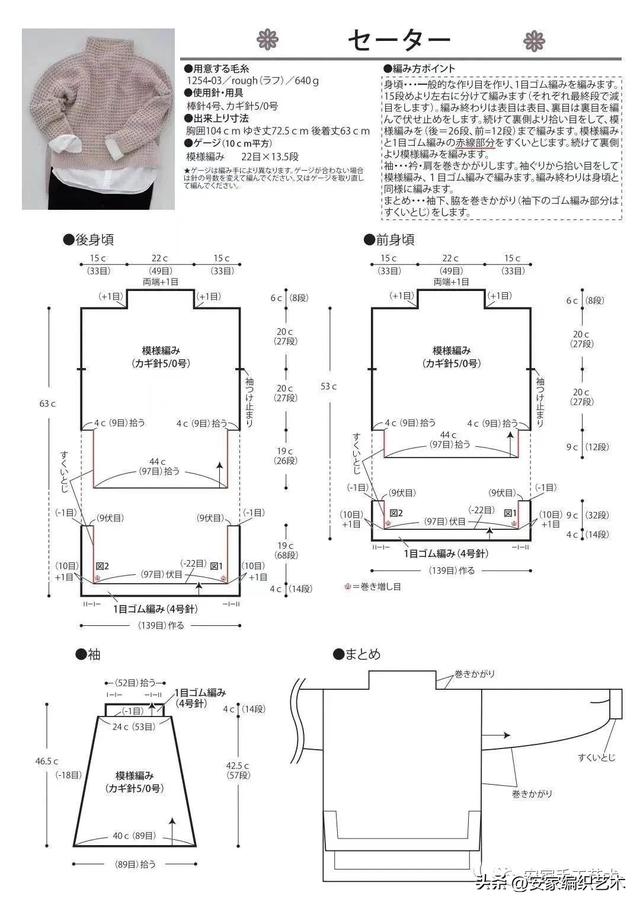最近有点疑惑,原因是遇到不少讲茶文化的人,他们似乎很真诚地说,如果不讲文化,茶只是两片树叶,说得我服膺不已。但当我要停下来听他讲文化的时候,他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因此,我这疑惑就不免滋生起来。
又有人说茶,口气大得如有神助,加上一本正经,茶被他这么一提搂,也是一副治国平天下的气度。此公的茶演讲进行下去,就只剩下义正词严、不容置喙的训诫了。
有个设计师朋友,说他以前做设计,主要客户来自于化妆品领域,这个领域追求外在有些着急,内在难免慢待,他就有些失望,就决定转移到其他行业上去,对,他就转到茶行业上面去了。
茶行业的所有人都在讲文化——他心想,这下好了,终于从糠箩兜跳进了米箩兜里了。进去一看,还是免不了失望,茶人讲起文化来,大都如同叶公讲龙,难免鱼龙混杂,真龙来了,就只好逃掉。
不讲文化的行业,乱相就多:无良的人就会来趁火打劫;茶人之间会为鸡毛蒜皮的破事相互攻讦、自寻烦恼;各种割裂传统的“伪创新”就会劣币驱逐良币,贻害茶业,贻害社会。
我是在峨眉山下长大的。峨眉山的茶,几乎像奶水一样喂大了我,我的味蕾对家乡的茶无解。
高山云雾瓦屋雪;
紫笋青衣东坡茶。
这些都跟峨眉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最能说明峨眉山一带的茶文化面貌。对此,我有比较独特的感受。
高山,峨眉山3099米,据说还在长高。
云雾,这几乎可以不用说,金顶的佛光,没有云雾大概不成。印度洋西南季风一来,大概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水分充足增加了云蒸雾罩的可能;降水量大增;气温上升又让高山积雪融化成水,奔漱而下,流经茶园,茶就摇身一变,变成此间有、他处无的好茶了。
瓦屋,跟峨眉山相互成全,联成一体,它们是一座山的两面。
峨眉山一带的笋子从紫色土里拱出,别有一种独特苦味;峨眉山一带的茶也从紫色土里拱出,也别有一种苦味,这苦味常常被外茶所攻击。殊不知恰是茶的正味,我怀疑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那一句反问“谁谓荼苦?其甘如荠”是专门替峨眉山茶代言的(峨眉山茶苦后回甘,被人选择性遗忘了)。当然,苏东坡干脆就把紫笋说成茶了,因为茶也有笋子般清新的苦味。
青衣是一条江,你可不要把它跟峨眉山割裂开来,李白不答应:“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平羌江,就是青衣。
东坡先生某种意义上也是峨眉山的。老师欧阳修有一座石屏,上面的景致可以是这样解读,也可以是那样解读,可是东坡先生肯定地说那是“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就连他贬谪黄州,最倒霉的时候想家,也要顺着长江往上面回溯的。他给自己打气说:“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汲水回家,煮一壶茶,服下,原力加持,黄州的苦难就化解掉了。
前几天读教育家叶圣陶先生的著作《我与四川》(这是他的儿子整理后出版的,书名未必是叶老先生所命),收获不小。抗战期间,叶先生携家逃难,来到四川乐山,经历了日本飞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差点家破人亡。稍安定,他就打发孩子们游历四处,增广见闻。有一次,孩子们回家,给他带回了峨眉山万年寺的茶。他一喝,惊喜得魂都跳出来了,觉得比起浙江、云南的茶来,这个茶实在是清趣无比,他马上打定了游历峨眉山的主意。该书第89页原话为:
带回山顶万年寺自制新茶,清酽芳洌胜于上好龙井,西行以来,仅尝此味。我们平常喝云南沱茶,浓而已,全无清趣。
是的,现在茶品太多,哪一种最适合做国民饮料、对身体最有助益呢?不好说,每个人的体质水平各不相同。我本人觉得,还是那种加工环节少、刚采摘的茶更靠谱一些,作为绿茶的峨眉山竹叶青便是其中的一种。
去年讲学,伴手礼就是来自家乡的好茶。我记得在甘肃嘉峪关,跟一帮文学圈的朋友交流。我那时候给当地一家军工企业写了一个战争与和平关系的赋,那个交流就是从战争说起。我说,北宋从初期到后期与西夏发生战争,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好多都发生在甘肃的土地上,这是悲剧;但是,每当战争一结束,来自我家乡的茶叶就几乎在第一时间出现,担负起了抚慰战争创伤的使命。我统计过,在相对稳定的时期,我的家乡四川每年要运送大概四万驮茶来到西北,每一驮超过一百斤。也就是说,总数超过四百万斤!最多时可能达到过六百万斤!
我说,和平,是茶叶贡献给世界的最美的礼物,不仅施于族群、国家,也施于单个的人——一个人内在的和平,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我说,我家乡的茶,因为名山大川的孕奇蓄秀,有仙气。
甘肃的朋友后来跟我说,峨眉山的竹叶青,清气十足,茶力绵绵,生趣盎然,好喝。
得评!本来就是一款无限清趣的茶嘛。
张花氏(作家)
(张花氏,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苏轼研究会会员。作品《与苏东坡分享创造力》《东坡茶》《寻找蓝星下的熊猫王国》等。)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ihxdsb,338640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