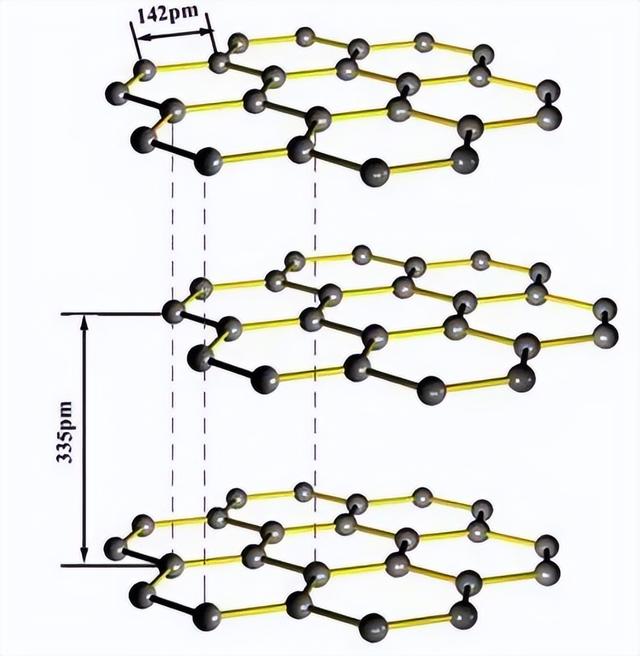作者 | 黄霸刀
整理柜子的时候发现一个包,长方形,梱绑得严严实实,像一块大砖头,一时想不起这里面是什么东西,解开尼龙绳子,打开外包装,是一叠杂志,几年前的《新华文摘》。
愣了一会儿,想起来,这是自己做的临时坐垫。当时孙子还没小,坐在桌边吃饭够不着,便用这个垫上。孙子长大了,不用垫子了,便随意放进柜子,一放就是几年。
随手翻看,发现几乎每一本都留着我当年阅读过的痕迹。我读书喜欢在上面做记号,或划杆杆,或打圆圈,而当时时兴一种彩色透明的水笔,把喜欢的句子段落划上,有浅绿、粉红、桔红,大都是浅绿。
我索性静下心来,把留下记号的文章再看一遍,竟然如第一次阅读一样,感受到其间的冲击力,《中国古代文明中人的问题》《社会硅谷:社会创新的发生与发展》《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
我在刘心武《巴金与章仲锷的行为写作》一文中停留了许久,我不应该作了记号却又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作家写作,一种是地道的文学写作,如帕慕克写《我的名字叫红》;一种则是行为写作,巴金当面鼓励我这样一个当时的新手不要畏惧松懈,把写作坚持到底,并且作为影响深远的文学刊物主编,在有特殊意义的复刊号上向我约稿,这就是一种行为写作。”
紧接着作者提到上世纪60年代巴金的另一次“行为写作”:
“《收获》曾刊发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游击队员辛俊地,他和成分不好的女人恋爱,还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地去伏击给鬼子做事的伪军通讯员,将其击毙,没想到那人其实是八路的特工……让我读得目瞪口呆却又回味悠长,原来生活和人性都如此复杂诡谲……
这样的作品,在那个不但国内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国际范围的反修正主义也越演越烈的历史时期,竟能刊发在《收获》杂志上,不能不说是巴金作为其主编的一种‘泰山石敢当’的行为写作。”
我们从这里看出巴金作为文学前辈的“行为写作”,一是有地位,二是好心,三是有水准,独具慧眼,四是有勇气有胆魄。
讲巴金之后刘心武讲到蔡元培,意思是说,人们未必记住他的著作,而他在北大的所作所为却至今让我们津津乐道。
如果跳出文学界,把视野放到一般人身上,仍然有“行为写作”。我们常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小说。
也就是说,每个人实际上都在用他的所作所为书写人生,都在进行着“行为写作”,只是不自知,或不为人所知而已。
其实,一个人的行为写作,不必一定要让人知道,但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只要你做了好事,总是有人会记住你。
有位朋友对我说,他能有今天,一是自己努力,二是有“贵人”相助。
“贵人”好几个,在他人生的关键时刻,都公正地对待他、提携他,让他从一个中专毕业的小学教员到一个政府机关的处级干部。这其间,他没有送过任何东西,哪怕是一包茶叶。
他无从报答,他们也不需要他的报答,他只是在心里记住他们的好,努力地工作,尽心尽职。
我想,这位朋友人生中的那些“贵人”,并没有想到要让他记住,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他们不是刻意的“行为写作”,却成就了一篇很好的文章,成为传统“贵人”说的精彩注脚。
对于“行为写作”,刘心武是有感而发,巴金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贵人。他说作家有两种写作,我想所有人都有两种写作,即职业写作与行为写作,行为写作是职业写作的基础。
如老一辈人经常教导我们的,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
每个人都在书写自己的人生,年年月月日日,一言一行,点点滴滴,有意无意,不求闪光,但求无愧。
所谓“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是也。
对于这一叠杂志的去留,我犹豫了好一阵子,它们的留本来是无意的,如果不作为孙子的坐垫,也许早在几年前就当作旧报刊卖掉了,消逝得无影无踪了,而如今,却因为重读而生出些许感叹,些许文字,些许留恋。
对于这无意中的“行为写作”,我有点失措,不知道该下什么标点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