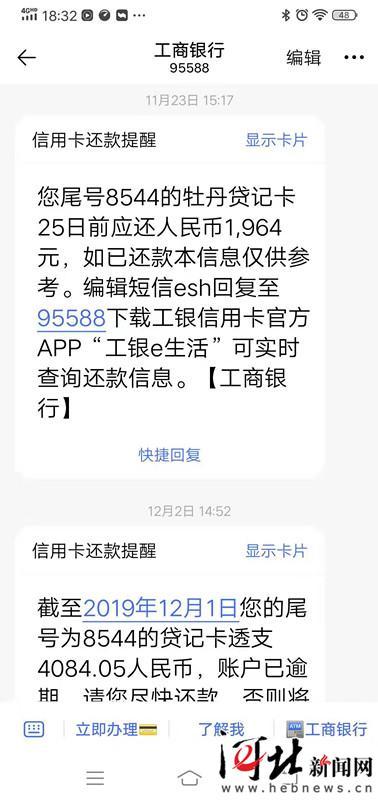只有三天,距离三天,连三天都等不到,闯不过的三天,最后的三天,便是母亲节。
准备做母亲的人,在为母路上的,已经做过多年母亲的,或者更是母亲的母亲了的,即将迎来一个伟大、祥和、温暖的节日。心中充满期待和喜悦的盼望,因为9号,是康乃馨的世界,是儿女们对天下母亲最完满祝福的一天。鲜花、礼盒、愿句、赞言,铺天盖地,欢愉无限。即使不能面见团聚,哪怕在音频里相对说笑,传递一声问候,也算亲人安好,互相开怀。
可是,昨晚,闺蜜大姐樱子来电,声音颤抖,心情沉痛,语调断断续续,她说“蘭子,你大娘、走了……”
我,良久,没反应过来,不知道听没听见她说,还是听见后大脑突然进入空白状态,空白的只有大幅的黑暗,失去了清醒意识的本能,不愿意相信,去真实面对又一个亲人的离开。
樱子那边,死寂的静,再也听不到任何声音,仿佛看到她满脸泪,也知道她的弟弟妹妹都在,邻居,乡亲,和帮助料理后事热心的送客们。
那种静,似乎不跟声音有关系,跟一个原本生着的人灭了的心跳关联。当亡魂正一丝丝抽离肉身,慢慢脱开一具骨骼,洒泪告别一个灵性的瞬间,那种静,是逝者对这个人间最后的回眸,在她不想永久闭紧的那双疲惫、痛楚而满含流连的、不舍的、艰难的眼神里,静,是她对生命最尊重的告白。就这样,一个从我出嫁就再没见过的亲人,一切的来不及里,走了。
大娘是众多婶婶中的美人,个高,皮肤白皙。只有茉莉玉容雪花膏、万紫千红的香脂年代,她什么都不抹,天生丽质,齿皓唇红,单眼皮的大眼,脚方手长,不胖,而且最扎眼的是与生俱来的基因卷发,波浪不大不小,恰当好处,发长过耳,剪齐,上瘦下蓬,像一顶夸张的大蘑菇。
那年间,乡下人哪里知道什么是烫发,无论男女老幼,都是相互对剪,女人使剪布的剪刀,男人用推子,剪成啥样谁都不笑话谁,无非因头发长了而剪,不为发型去修理,没审美概念,庄稼人,简单的日子,清澈的心际,祖祖辈辈的朴素。
大娘不同,那头发纹理,像香脂盒上的美妇。只是图片中的女人更显艳妖一些,电烫的发卷张扬的翘起燕尾一样的发尖,发丝油亮,鬓边别两根彩色卡子,另插一支丽红的玫瑰,鲜亮的旗袍下,半露莲藕一样的小腿,踩高跟鞋,人面桃花,朱唇微抿,正揽镜梳妆。
大娘长得跟她们一样美,虽然差那么一点点,只不过因没如图上的浓妆而已,若也涂抹,恐怕真就相似的重叠了。
大娘性格内敛,非常不爱说话,每次去找樱子一块上学,她的表情和眼神便是语言的形式,她格外的不擅言谈,似乎成了熟悉她的人们的记号,如“那个不说话的人”,指的就是大娘。她的温柔、无力、和一脸体弱的气色,或许就因为她出奇的白净,从小时候到今天,段氏家族中的上一辈人,根本从来,就只属她了。嫁给粗犷矮小、肤色麦黑鼻子像鹰嘴的大伯,一对农村夫妻略带讽刺意味的典型配搭,天大的反差暴露无疑。真成了一句老谚语:好汉无好妻,赖汉娶个花织女。
如此安静的大娘,寡言,从喊她第一声,到记忆的节段,真没见她发过一次脾气,连指望听她一句大声说话都不会。上帝其实最公平,尽管并没给我们分工,和教会我们怎样中合缺陷,互补性格,但大伯大娘这一家子确实被上帝平衡得几尽完美。大伯爱暴躁;樱子净高嚷;妹妹嗓子像不定时的海豚音;弟弟一着急额上脖子里的青筋一根一根跳出来。唯独,沉着,安稳的大娘,一个“静”字震住一切,一个“默”字,熨平全家。
近八十岁的老人,被恶性肿瘤索走了性命,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即使修炼一辈子的“静”也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不知道病重的大娘头发是否依然如花,发丝的波纹还如喇叭花的藤须一样柔软美丽。
她婉弱的一生,娇情的外表,可能早已埋下今天大病的隐患。记得她很少下地干活,不出门,也不怎么出屋,最多的印象,总缱绻在炕上,守着该缝的布衣,纳到中途的鞋底,一只枣红色的针线篰箩,里面有白线、黑线、板扣、松紧带、顶针、锥子、剪刀、鞋样、子母扣、鞋带、袖头、绳子、花花绿绿和黑白灰的乱布条。那些都是她静中的内容,不说话的时光,心中有数,手里不停,除了因高而生就的长腿,陪她终日弯曲在温暖的土炕上,避免了风吹日晒。极少的田间地头,使居家、恋家、护家的她,脸色更加苍白病态,再没有少女时红苹果的健康脸蛋。
她是个不禁寒且耐热的人,冬衣总比别人多续一层棉花,裤厚圆滚,暄乎,一把抓不透,穿早脱晚,从秋后到春末,虫蝶满处飞,她才换上薄的。四五时年代的人们,心存封建思想的人说。娶媳妇别娶好看的,不仲用。找五大三粗身型丰满的,能干。说不清楚,大娘是不是因为长得好看,才没力气干活。难道有没力气的说法就是针对丑俊而言的吗?真有关系?还是古老的执念铸成一种论道的偏见。
想回去送送亲人,痛绝的想,万分,心中悲伤。可是,我回不去,有特殊原因。
这种时候,大娘尸骨尚温,多想再看看她曾经美丽的脸,摸摸它蓬松应该再不黑柔的卷发。病疾的折磨会让一个完好的人容颜尽失,脱型骨露,好在,她才仅仅卧床一个月,癌细胞就疯狂漫延全身,乃至扩散进头部。上午,流着泪问妹妹,大娘走时有没呈现巨大痛苦,她说,没有。因为已经没了感觉,不呻吟,不叫疼,从依旧的安静中,放开了生命;从极度昏迷中停止了呼吸。也好,她没有改变自己始终的天性,无声无息,悄悄,割舍了亲人,像一缕轻轻的风,随万花凋零,在春天的背影里,带上安然淡定的自己,如一片早衰的叶,从容落下,落在五月的臂弯里,待又一个宁静的自己重来这个世界,便是树下那丘新堆的黄土,一场悠然的雨过,几根鲜草点缕干裂的坟头,当野花在深埋的灵魂一角,慢慢吐出温润的腮红,又一首凝幽的心歌,在铺满月光的墓碑前,清唱。
只是,她走得太急,匆匆忙忙还没看到节日的康乃馨,就一脚踏上远去的不归途。再也不能转身。不知多年前,大娘家东窗下的手绢花还在不在,我曾浇过水,和樱子一起。如果那棵花尚茂盛,这会该连绵成片,甚至开满了那座好久没走进的院子吧。
按家乡送灵习俗,今晚12点,大娘您
便可以迈进自己彩色的轿车,带上金童玉女,还有百宝箱,手提袋,新裙新鞋,万两纸钱,在亲人为您开设的另一条通往阴间的大路,放心启程。千万别回头,您的家已经迁去天府,那里是无忧的天堂。
去吧大娘,轻松上路,从此,再没疾病缠身。我们会想念您。盼来年,您的荒冢门畔,开满嫩黄的雏菊,雪一样的雷神花,大家会去看望您的,依然是母亲节来的前夕。
愿,最后的康乃馨陪您天堂幸福,温暖吉祥,大娘,一路平安!
作者
河北衡水安平人
蘭冬子
一个心存怀念,感伤离别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