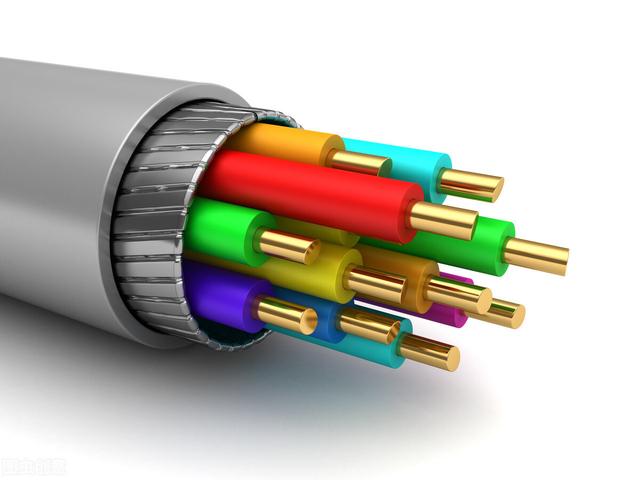文:宿夜花
2017年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相爱相亲》是近年来一部高口碑的话题之作,电影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编剧奖,豆瓣评分也高达8.4分。电影时常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三代人爱情观、婚恋观的佳作。
事实上,《相爱相亲》所讲述的主题已经不限于不同代际之人的爱情观,更是讲述了广义上的“爱”。既是时代的变迁给人思维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在体验领悟“爱”中与生活和解、完成自我的成长,那种体味个体生命孤独之后的豁达与从容,更使人动容。
三代女性的爱情观无论是片名“相爱相亲”,还是英文名“Love Education”(爱的教育),都用了非常通俗的语汇从感性的视角切入。相亲之人是否一定相爱?这也是电影情节的核心冲突,慧英与阿祖双方的矛盾根源。“相亲”的乡下原配用一辈子的等待赢得了乡邻的尊重,却永远没等到出走的情郎;“相爱”的城市妻子相守一辈子却无法合葬,电影通过一场迁坟的争执展开了几代人爱情观的探讨。
事实上,《相爱相亲》的主题并不止于爱情婚姻与血统亲缘建构的家庭情感世界。张艾嘉用一种深远的视角探索时代变化之下人的变化,颇有几分宏大叙事的意味,设立了多组二元对立元素: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梦想与现实、封建包办婚姻与现代自由恋爱等。
因此,电影所探讨的三代人婚恋观以及女性的价值选择更有现实意义,而非空中楼阁。不仅仅是对前作《20 30 40》女性自我认同与价值归属主题的一次强化,更是摆脱了前作《念念》中闪回隐喻等“意识流”手段,表达上更为平实却不失力度。
“她相信一辈子,我相信一句话,你只相信一刹那。”
祖辈的姥姥阿祖,正如无数传统女性一样,践行的是乡土社会中的女性道德准则,恪守妇德,尽孝道,在丈夫背弃的情况下照顾公婆。她将“家书”视作“情书”,信上的一句问候,一张照片,一副用家乡女性文字绣出的丈夫名字,都可以伴随她度过无数个等待的漫长夜晚。纵使她所守护的并非是现代观念下的爱情,但她执拗地守候仍旧让人唏嘘不已。
中年人的爱情观,是一种激情消磨殆尽后理性感性调和下的温情脉脉。田壮壮饰演的尹孝平与张艾嘉饰演的岳慧英,他们之间说不清是爱情更多还是亲情更多,他们婚恋观既不似姥姥般传统也不似女儿的开放,是一种在柴米油盐与人生百态中磨合出的一种处世哲学、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年轻人的爱情,充满激情,他们渴望跳脱父辈的条条框框、脱离原生家庭的束缚、追求自由与理想。正因如此,他们的婚恋中更有种捉摸不定的不确定性。薇薇男友阿达特殊职业摇滚歌手的设定,更使得角色自带一种漂泊的属性。
电影在讲述三代人爱情观时,并没有给予绝对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三种爱情形态的背后引发对女性价值选择与情感归属的思考。是恪守无爱的约定固执执守,还是将其蕴于一种看似庸常的琐屑之中,亦或是为了忠于内心的那份自由之爱不惜一切的追逐?
电影没有给出答案,从阿祖对外公的精神依附,到慧英对丈夫的强势,再到薇薇为了爱自由选择,现代观念下女性的独立自主的轨迹却是鲜明的。电影也并非简单停留在对狭义之“爱”的探索之上,而是探讨了除了爱情外一切形式的“爱”,人与人间各种形态的爱,以及人对生命的感悟。
女性中年危机背后的身份焦虑张艾嘉:“当我们在这个大环境中游荡的时候,如何可以更自在地跟自己相处,这是我的电影想要探讨的问题。”(语见一起拍电影:《相爱相亲》浓缩的中年女性危机更值得关注|专访张艾嘉)
对“爱”与“亲”的感悟滋生出了关于自身的焦虑,电影将重点放在中年角色,张艾嘉饰演的慧英身上有许多女性中年危机的典型性。
她即将退休,有种不甘落伍的焦躁;与丈夫感情陷入一种不咸不淡的平淡之境中;看似张狂与强势,实则内心异常脆弱。她心中的最大心结即是她认为自己是父母亲真正爱情的结晶,并希望通过迁魂使得母亲的地位更名正言顺,她迫切需要的是对父母之爱并与之相生的家庭合理性的一种认同、争夺的是母亲与自己对父亲家庭的话语权。
当她从单位到街道办四处奔波,却无法高效证明父母是合法夫妻,这种荒诞的黑色幽默与第五代著名导演黄建新《谁说我不在乎里》里冯巩与吕丽萍倾尽全力都无法证明夫妻关系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种身份焦虑同样在阿祖与薇薇身上。阿祖用自己的方式,搬出族谱、乡长等传统乡绅秩序下的话语代表试图证明自己婚姻的合法性,却也很难取得现代话语下的有效认同。薇薇与阿达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也时刻面临金钱、他人、各自处境的冲击,因此薇薇也面临着与姥姥阿祖同样的处境,如果阿达追逐梦想去了北京她或许重复阿祖的宿命。三代人对身份的焦虑折射出了一种婚恋中的普遍困境,而她们之间又用“爱”完成一种和解,走出各自的人生困境。
个体的绝对孤独与世俗生活中的和解张艾嘉曾在访谈中谈及创作初衷是为了讲人、人的故事:“不只是感情的东西,而写到人的变化。我们就是这么小的一件事,可以影响到别人,可以谈到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可以谈到人跟环境的关系,甚至于很多现在整个社会的变化那么快,会影响到人的作风跟人的思维。”(语见豆瓣电影观影会客厅张艾嘉访谈)
关于时代变迁下个体的永恒孤独,是影片在婚恋观、家庭伦理等表层主题下所探索的隐性母题。在房间内,至亲的一家三口,躺在三张床上,同样的手机,同样的动作,却无法完全理解彼此的内心。如果说孤独是亘古不变的人生母题,那么当现代科技与现代媒介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剧了这种孤独感,这使得这种孤独母题有了更鲜明的现代性。
对现代科技与媒介的焦虑贯穿在整部影片中,当现代传播方式将人的一切苦难与迷惘以一种奇观的方式呈现于他人眼中,以此满足大众的浅层自娱,任何人生的悲欢与苦难都成了一种“奇观”被大众消费。因此,阿祖的“护坟”与乡下的贞节牌坊都成了一种消费工具。
无论是西德尼·吕美特那部获得奥斯卡奖的《电视台风云》,还是许冠文、萧芳芳黑色幽默喜剧《抢钱夫妻》,从电视的兴起,关于现代媒介“娱乐至死”的寓言便一刻未停息。因此,《相爱相亲》呈现的是一种隐忧,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当下尤甚,当浅娱乐逐渐代替一切严肃思考,人内心感受到的更是一种异化后的空虚与孤独。
个体的永恒孤独、个体之间绝对理解的不可能性在当代娱乐话语下、几代人的冲突磨合之中使人倍觉无力,而他们之间也正是在体味到个体生命独一无二的孤独感之时逐渐达成彼此的和解。
当阿达躺在棺材上体验死亡的那刻,他哭了,对未知的迷惘、对死亡的恐惧、个体生命无法被绝对理解的孤独汇聚成了一股吞噬人心的力量;旋而,他又露出了笑容,这是释然的微笑。当阿达用一种极富仪式感的行为体验生与死之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悲悯与感动,是勘破生死的豁达,在生老病死的轮回、生命得失的无常中,每一个孤独的个体都用自己的方式、固守着理想、坚持着自己的一份执拗来完成自己人生的进行曲。
美国作家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曾引用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的诗歌:“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
因此,当体会到了个体生命那份不被理解的困境之时,他们开始尝试着一份包容与理解。因为阿祖与慧英彼此的理想都是为了自己的“爱”与“亲”有个归宿,当阿祖最后一次说出了那句“我不要你了”并决定“进城”的同时,慧英捧着骨灰盒“返乡”,这种彼此间的和解更显得动人。
除了个体间的普遍困境产生的灵魂共鸣外,这种和解也是建立在世俗生活中的人性美好之上。当阿祖看到阿达青春的面孔而露出了一种自发的并略带羞赧的笑容之时,我们很难说究竟是什么力量感染了她,是青春生命的活力?男性的阳光与硬朗?还是人与人之间心无城府的信任与理解?
电影的结尾从关于生命孤独的深远主题重新拉回到世俗生活的悲喜之中。当车上的丈夫劝慰妻子时,妻子感动之余终于释放心底压抑已久的醋意“以后不准王太太坐这个车子!”;当尹孝平五音不全地唱着崔健的《花房姑娘》时,岳惠英只一句“你唱歌为什么还是那么难听?”,泪水中带欢笑。
影片中诸如此类的生活化、心照不宣的幽默细节还有很多,夫妻间争风吃醋、母子间吵架斗嘴,用世俗生活中两性、亲人之间看似拧巴实则充满趣味的温情,中和关于生命孤独、身份焦虑等严肃命题,是影片的一大特色,使得影片不会过于显得晦涩与沉重,充满了生活质感与生命情趣。
© 本文版权归 宿夜花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