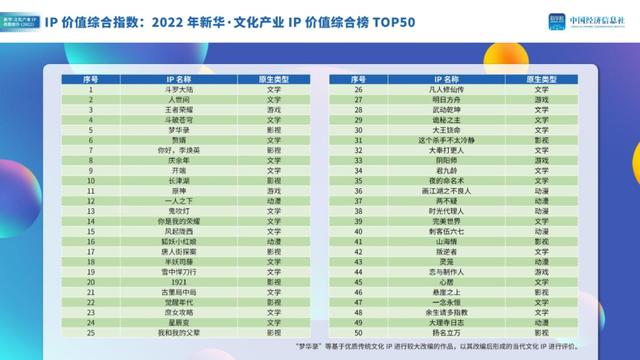祭的本义,无非是“追养继孝,君子将以祭之也”。祭礼的本义,则为“报本追远”。其背后蕴涵着两层意思:一是此身得自祖父母,又依赖先人之泽,才能享受余庆,平常朝夕奉养承欢,而一旦故去,无法尽生孝之责,心中悲思无以寄托,所以就借助祭荐之礼以申子孙孝道之情;
二是做子孙的因为贫贱而不能在生前供菽水,尽孝道,如今自己已经发达鼎食,而亲人已不再能享受,心中悲思莫及,所以借助祭荐以志子孙悔悟之情。
显然,原始的儒家祭礼并无借助先人游魂虚位佑护之心,换言之“求福”并不是祭礼的原始意义。明代祭法,明初纳胡秉中之言,采用一种庶人祭三代、士大夫祭四代之法。其法如下:庶人三代牌位,曾祖居中,祖居左,祢居右;士大夫家庙四代牌位,高祖居中左,曾祖居中右,祖居左祢居右。
祀祖先的礼仪按照《家礼》,四时应祭四代。冬至祭始祖,春祭先祖,季秋祭祢,宜随时举行。至于像上元、端阳、中秋、重九之类的俗节,则应奉献“时养”。根据传统的祭礼,每当祭祀前一日,须斋戒陈设祭器,备具祭馔,预先从子弟或亲友中选择知礼的人为赞祭。
洪武二年(1369)三月,明太祖命朱升定祭祀前的斋戒之期。于是,朱升奉敕撰写了《斋戒文》,其中对斋戒的含义以及斋戒之期提出了以下看法:“凡祭祀先斋戒而后可以感通神明,戒者禁止其外,斋者整齐其内。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不理刑名,此则戒也;专一其心,严畏谨慎,不思他事惟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此则戒也。大祀斋戒七日,中祀斋戒五日。”此文进献给明太祖以后,太祖认为帝戒之期日久容易让人产生懈怠,最后定为不论大、中之祀,一律将斋戒之期定为3天。
祖先的祠堂,必须时常保持凊洁。到了朔望,就要去祠堂参拜,有事则告。出远门,到祠堂禀告祖先,返回亦同。有了丧事,也不可废祭,但须易服举行。祖先的神主,由宗子奉祀,支子只随班助祭,不得僭祭。当祭祀时,必有篇祭先的祝文。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御制祝文,成为天下祝文的范式,不妨引述如下:
维某年某月某朔某日,孝孙某阖门眷属,告于高曾祖考妣灵曰:昔者祖宗相继,鞠育子孙,怀抱提携,劬劳万状。每逢四时交代,随其寒暖,增堿衣服,撙节饮食。或忧近于水火,或恐伤于蚊虫,或惧罹于疾病,百计调护,惟恐不安,此心悬悬,未尝暂息,使子孙成立,至有今日者,皆祖宗劬劳之恩也。虽欲报之,莫之所以为报。兹者节届春夏秋冬天气,将温热凉寒,追感昔时,不胜永慕。谨备酒肴羹饭,率阖门眷属以献。尚享!
这篇御制祭先祝文,当为明代民间普遍使用。玩其文意,追溯祖宗鞠育劬牢之状,可谓痛切沉止,直通幽冥,很符合明太祖朱元璋的心态,当为亲自制作,不可以文字工拙加以衡量。
除了家族祭祀,皇族还得祭祀皇陵。明代皇帝陵寝分为两处,主要是在北京的天寿山,在南京的只有太祖的孝陵与懿文太子的寝园。懿文太子陵园在孝陵之东在明代后期多称之为东陵。
南京皇帝的陵寝,朝廷也有一套定期的祭祀制度。这种陵寝之祭,相当于民间的墓祭。太祖的孝陵是一岁三祭,即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此外,如忌辰、万寿圣节、十月初一,也有行香之礼。祭祀之时,均由百官陪祭,由守备武臣行礼,后例遗司香勋臣行礼。
而懿文太子陵寝却是一岁九祭,分别是正旦、孟春、清明、孟夏、忌辰、孟秋、中元、孟冬、冬至、岁暮。究其原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沿习洪武中的旧礼行之之故;二是建文帝被追祀时,加隆祢庙,才导致有此缛礼。
在南京,还有两座仁宗妃子之陵,每年也行陵寝山祭之礼。一座在牛首山东的观音山上,为贞静顺妃张氏之坟;另一座在吉山东的南山上,是悼熙丽妃李氏之坟照例每年祭拜六次。
永乐九年(1411),正值明太祖的忌辰,明成祖亲自率领百官恭谒孝陵致祭。这说明明初有皇帝亲自祭陵之例。孝陵离皇城不过十多里。迁都北京以后,山陵建在天寿山,离京城有百里之遥,所以凡是遇到清明、中元、冬至三节,虽仍有像宣宗于宣德元年、五年(1426、1430)亲自至天寿山谒长陵、献陵的例子,但一般只是令勋旧大臣至皇陵行礼,已再无皇帝亲自致祭之例。至嘉靖朝,才重新定皇帝亲自至山陵致祭之制并且将其定为清明、霜降两节致祭。
接下来是民间的祭祀。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祭礼的实施由家庙祠堂来体现。家庙之礼只是祭祀高、曾、祖、考四世,自朱熹的《家礼》以来,直到明代朝廷所定祭礼,大体均是如此。在明代,家庙、祠堂之仪只是行于土大夫或富贵人家。据载,在松江府上海县,如潘、陆、乔等姓缙绅之家,家必立庙,设祭品,四时致祭。致祭时,主人必穿公服,准备牲牢,奏乐,子孙内外全谒庙,自岁时以迄朔望,均是如此。
在乔氏家祠内,椅桌也按昭穆相分,不加移动,如夫妇二人者一桌二椅相连,三人者一桌三椅相连,左右各分屏障以使“代不相见"。在杭州,张瀚家也设有家庙,岁时伏腊忌日,必衣冠而祭。后又创建宗祠,祀高祖以下神位。每当祭祀时,遍召宗人,聚集在宗祠下。祀毕,在前堂享胙。张氏宗族还有宗约,就祭祀之事作如下规定:“凡我同宗,月轮一人司香。元旦必集,春秋祀必集,毋以事免。"
在明代,死者之忌日,已经清楚地分为“生忌”与“死忌”两种。死者死亡之日,就是“死忌”,又称“暗忌";而死者出生之日则为“生忌”,也就是“明忌”。生前生日有做寿之习,那么,死后遇到生忌之日,也会给死者做寿,称为“暗寿”。如江西南昌的朱氏宗室,尤其看重“明忌”,“亲死者遇十生日,如五十、六十之类,犹追寿焉,族人具礼谒贺,一如存日”。此为暗寿之例。葛祭需要指出的是,在明代,祭礼不过存在于宴贵大族中。至于一般小户人家,率多朴野,不知节文。
在北京,每当清明节,无论贵贱,都带酒肴上坟,男女盛服前往,大体就是古时墓祭之意。墓祭并非上古之祭,而是始于汉代。按照传统的说法,墓乃体魄所藏之处,而非神魄所聚之处。但正如明朝人吴廷翰所言,古人所说“魂则无不之也”,那么神之所藏固然在庙,但也未必就只在庙。况且庙中仅以木主为神,那么人们求神于体魄之处,也未尝不可。
墓祭之礼,行之已久,人情安便,也正好符合“礼以义起”的道理墓祭之俗,最常见的是在清明、重阳两节上坟扫墓,已成明代普遍的习俗。惟有河南延津,在此两节之外,正月初三、七月十五、十月初一三天也属上坟之日。十月上坟,称为“送寒衣”。
一些有官封的家庭,在墓祭时,更是行“焚黄”之礼。此礼始于宋代。在墓旁焚毁者,为一些明器、人马仆从之类墓祭烧纸钱之俗,在明代也广泛存在,只是各地稍有差异。在浙江绍兴府,一些妇女生前就到庙里烧纸锭,一烧就是百两,说:“以是寄之冥司,死得用之也。在福建前田,每当中元节祭祀祖先时,往往也盛行一种给祖先烧银锭的习俗,冥纸上全印有“京宵花银”匹字。
明代墓祭之俗,南北稍有不同。北方人颇重墓祭,尤其是山东每当寒食之时,郊外哭声相连,至不忍闻。当墓祭之时,一些善歌者还唱白居易的《寒食行》,作变徵之声,旁人听后,无不落泪。而南方人的墓祭,却已变为踏青游戏之日,纸钱未烧成灰,舄履相错,等到日暮,在荒野问主客无不颓然醉倒。
家礼祭祀既已废而不行,必然为神道所惑。所以,在民间,每当元旦,必在桌上设天地神牌,用牲果祭祀。家中多设家堂神位,画儒佛道三教诸神,显得淫而不雅。即使是稍微知礼之家,也不过是立一木主,上写“家堂香火之神”,或者称“天地君亲师”,而将祖先的神主置于其旁,并无昭穆祧祢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