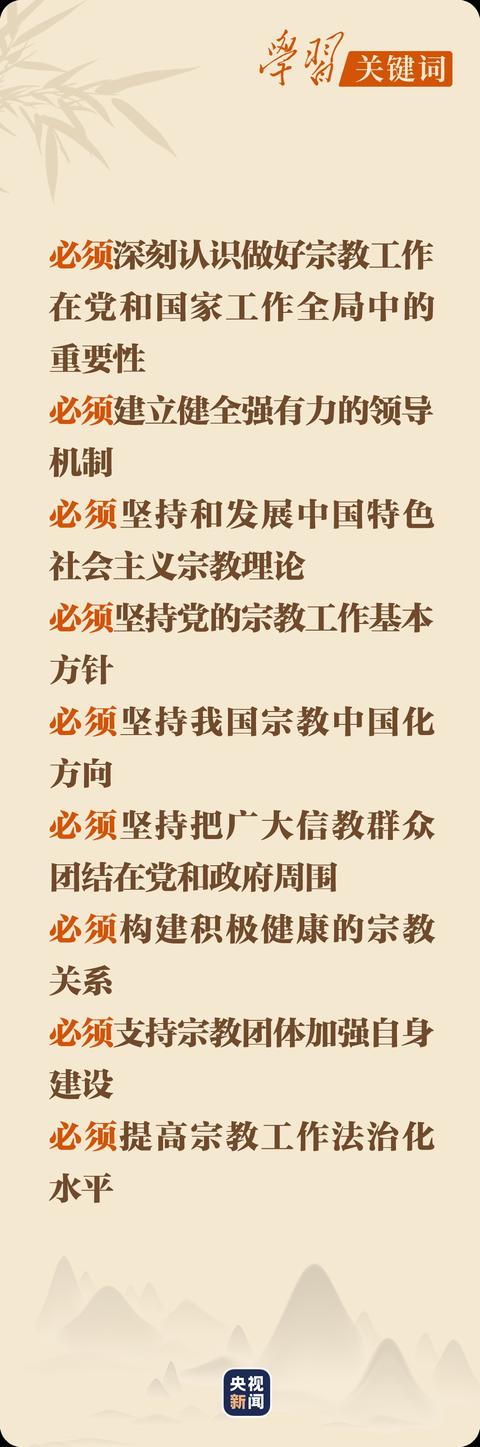作者 | 余雅琴、徐悦东
在不久前闭幕的FIRST青年影展上,争议最大的作品莫过于翟义祥的《马赛克少女》。这部反映14岁少女性侵案件的电影,在还未面世时就获得大量关注。此前,《马赛克少女》是多个电影创投会上的宠儿,更是首次以内地项目的身份斩获金马创投会议最高奖“百万首奖”。
然而,作为此次电影展首部展映的竞赛影片,电影一经面世就受到各种争议,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评价。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否喜欢这部作品,网络上对它的讨论都远远超出了电影本身。
喜欢这部电影的观众认为,这部电影塑造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少女受害者,视角独特,另辟蹊径。引入调查记者的角色,让这样一个社会案件的维度更加丰富。甚至,有人将这部电影和改变韩国法律的《素媛》或者《熔炉》相比,认为同样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关怀。
《马赛克少女》海报
口不择言的影展言论和始料未及的负面反弹
网上的负面评价,除了影片的叙事和节凑混乱外,还因为观众对影展负责人称“所有竞赛片豆瓣评分不应低于6.5,观众打分低于3星是不负责任等言论”的反弹。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制作人批评“豆瓣影评人”的事件。此前,冯小刚也有过类似的言论,同样激怒了网友。但是,这在秉持“欢迎拍砖”的青年影展上出现,则显得更加令人难以接受。电影评论应该是自由的,负责人的不当言辞,使得观众对该片的期待转为了失望,这些都体现在“豆瓣网”的页面上。
一些人分析,由于导演翟义祥的处女作《还俗》曾在第9届FIRST青年影展得到过“最佳艺术贡献奖”,《马赛克少女》又同样是该影展创投孵化的项目,首场放映结束后电影没能收获预期口碑,导致该影展负责人口不择言。
严厉的批评对一个年轻导演来说也许是需要勇气消化的,但是也或许是一个导演的必修课。当各种舆论和猜测来得如此快速和迅猛,最应该被讨论的其实依然是电影本身。《马赛克少女》所引发的争议与这部电影想要展现的复杂的舆论场与现实形成了某种互文关系。
《马赛克少女》豆瓣页面截图
从另外一个层间上说,在诸多的青年导演中,翟义祥算是幸运的:1987年出生的他,已经拍摄了两部长片,也受到不少支持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作为青年导演的代表,翟义祥对时代的观察表明了一种青年人对社会的回应。青年人关心社会,想要用电影和社会进行对话,也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天然的权力。从《还俗》到《马赛克少女》,他的作品都善于使用社会新闻作为打开议题的介质。
第一部片子《还俗》是他自己凑钱拍摄的,讲述了一个和尚还俗的故事,从寺庙到社会,和尚经历了魔幻现实般的洗礼。翟义祥想要表现的是,在这个价值观多元的世界里,人们究竟应该怎么自处的问题。
《还俗》剧照
电影改变了翟义祥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名气。他也坦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生活状况并没有因为拍摄电影而获得实际的改善。“那个阶段就想表现当时的精神状态,所以拍摄了《还俗》,不同阶段关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后真相”时代,电影对社会事件的处理面临挑战
《马赛克少女》或许不能算是一部成熟的作品,但依然是一部工业意义上来说制作水平精良的电影,影像呈现上也做了不少风格化的处理。在拥趸那里,这部电影有很强的现实主义关怀,在形式上也有创新。但是,我们也无法忽视电影在剧作上的漏洞和结构的失衡。这些可能让这部试图严肃探讨社会问题的作品的批判力度大打折扣,也让这部电影费心设置的非线性叙事丧失有效的艺术表达。
电影呈现出相对丰富的主题,打开了一个比较广阔的探讨空间。电影不单单是关心社会问题,而是试图用一种不同于主流的“真相观”,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面对一个女孩的痛苦遭遇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计算,被害者反而被打上了“马赛克”被遮蔽住了。由此,电影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所谓的受害人,一旦被打上某种标签,是不是也必须符合大众的想象呢?
不管是否是作者的本意,这部电影也许会被解读成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比如,电影让只有14岁的女主角说出:“头发是我的,身体也是我的。”宣言式的态度呼之欲出。矛盾的是,在女孩被家人裹挟着怀孕生子的过程里,她从未对自己的身体的变化表达出任何情绪,也没有对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
这或许只能解释为电影叙事的断裂和对角色塑造的缺憾了。如果作者想要在电影叙事上做出一些突破,也可能会牺牲掉电影完整的表达。在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承转契合和对人物的塑造,主人公的行为就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同。
这部电影势必也向观众提出挑战,一部电影应该如何处理真实的社会事件,如何展示苦难和不公?
一方面,我们必须要肯定它的现实价值,在这样一个“后真相”时代,这部电影对真相的追问和质疑依然有它的可贵之处。我们看到,今年的几部艺术电影,都以调查记者为切入口展开故事,电影人正在承担记者的角色,为我们进行着影像上的深度报道。
据翟义祥说,为了创作这部电影,他和调查记者一起工作,深度体验了记者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受到“马赛克少女”这样的当事人,往往被置于不被真正看见的位置,被各种来自周遭的压力所裹挟。电影想要传递的,本来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探寻真相过程中的外部世界。
电影塑造了一个“不完美”的受害者,我们在这个少女身上看到了人的复杂性。她的叛逆和不羁,或许也是造成她悲剧的原因;围绕在她身边的各种势力,也许更彰显了社会意义上的结构性伤害。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唯独没有展现凶手,是什么让一个女孩不能说出真实罪犯的姓名,而去指控他人的?这部电影也在挑战我们的道德观。这样一部涉及对未成年女性巨大伤害的电影,电影模糊了绝对真相的存在,强调未成年女孩的“主体性”,这是否触及伦理问题?
《马赛克少女》剧照
我们知道,电影本来的主角是王传君饰演的调查记者,可惜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角色在目前的版本中只剩下不多的戏份;在经过报社上级的打压之后,这个调查记者没有出现在电影的第三部分。在这部分里,电影的视角从记者变成了女孩,女孩被送入了一个社会辅导机构,并经历了同屋女同学的自杀事件。在电影的最后,学校组织合唱,女孩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哭泣,观众的情绪得到释放,电影也戛然而止,留给我们的是质疑和唏嘘。
在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设置弥补了前文提及的伦理问题。然而,再一次面临叙事混乱的指责,争议对翟义祥来说是可以预知的。早在电影首映之前,他接受《新京报》文化频道的采访时就说:“《马赛克少女》相应地做了一些影像化的处理,并在叙事上做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此买不买账。”
翟义祥的职业生涯,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下青年电影人的状态。在和他的对话中,他提到最多的就是坚持和妥协、资本和制度,这些宏大的词语是很多像他这样的年轻电影人思考最多的问题。思考这些,是一个中国电影人的敏锐,也是一个中国电影人的局限所在:当一个作者面对如此丰富的现实题材库时,到底应该如何取舍?《马赛克少女》的争议,也向所有中国作者提出了疑问。
中国电影一向有现实主义传统。这其中的原因,固然与我们理解电影的观念存在局限有关,但或许与电影从进入中国进而被中国人接受、观看、制作的进程中的历史现实有关。社会现实对中国电影的创作介入之深,使得电影总是被现实力量干预,但依然能够曲折地反映着现实。只是,这种反映所达成的效果却千差万别,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马赛克少女》,是一部有遗憾却依然值得观看的作品。
反转的社会新闻背后,是热衷于看热闹的时代氛围
新京报:你是怎么想到拍《马赛克少女》这样一个故事的?
翟义祥: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创作冲动。拍《还俗》,是因为那时候我刚毕业在找工作,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社会。我当时很不适应那样的环境,所以我拍了《还俗》。这个片子讲的是一个和尚还俗,进入世俗社会的故事。
当我拍完《还俗》之后,开始准备做第二部片子。如果说《还俗》所拍的家乡算是一个舒适区,新片则不再讲和自己相关的事情。那会儿,我每天都在上网看新闻,关注了很多案件,比如雷阳案、江歌案等。这些社会新闻都会出现好几个反转,特别出乎意料。不得不说,现在大家越来越趋向于看热闹。
翟义祥在电影展期间交流,FIRST组委会提供图片
后来,我看到一个女孩怀孕的新闻,整个过程也一波三折的。其中,好几个嫌疑人都被推翻了。几年之后,凶手确定为一个老头。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老头到底是替罪羊,还是真的罪犯。在这件事里面,大家期待的是反转,每次反转都给你一个真相。所以,我想,当事人在这里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
我当时还和一些社会记者聊这事。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记者在接近所谓的当事人时,其实没法真正地走进她的生活,记者只是一个旁观者。因为,我们只在乎真相。可我当时就想拍真实的人,在那个世界里的一个处境是什么样的。包括这个女孩的父母,也希望得到真相,却不关心当事人本身。所以,在《马赛克少女》里,那个调查记者跟他调查的对象之间有一个张力
《马赛克少女》剧照
新京报:你怎么看“少女性侵案”这种题材的电影,比如《嘉年华》?
翟义祥:有些人对《马赛克少女》有这方面的期待,但是这部电影和《嘉年华》是特别不一样的。我是拍摄完成后才看的《嘉年华》,《嘉年华》和达内兄弟的电影很相似,它在根本上讲现实。
而《马赛克少女》相应地做了一些影像化的处理,并在叙事上做了一些挑战。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对此买不买账。在讲述故事上,我们也没有像常规的叙事那样,去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我不想让《马赛克少女》变成《素媛》这样比较煽情的电影。
《嘉年华》的现实主义题材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嘉年华》已经非常侧重于叙事了,但还有很多观众觉得节奏比较慢。《嘉年华》里面有一些很电影化的东西,比如,象征的手法已经做得很成熟了。
《素媛》剧照
新京报:你觉得对你来说,《马赛克少女》的探索和挑战性主要指什么?
翟义祥:首先,如果我拍农村,我不想在一个传统的语境下,拍那种纯写实主义的中国农村。现在,农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叙事上,我想在影像的气氛上做一点尝试。
我们拍《马赛克少女》其实跑了四个省份,设计了很多和主题呼应的元素,包括“马赛克”这个概念,它的外在概念要有一个影像调性上的呼应。还有一点,《马赛克少女》与传统的叙事结构确实差别很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冒险,但我还是愿意尝试。
新京报:这个叙事上的冒险具体指什么?
翟义祥:这个事件,听上去是一个真相性很强的故事,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传统的给你定性一个凶手的故事,然后给观众解释,这个凶手为什么做了这件事。
新京报:这有点像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处理方式。凶手是谁,为什么这样做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展现出来的那个广阔的社会。你有没有参考过这类小说?
翟义祥:没有。当时我看了是枝裕和的《第三度嫌疑人》,那种感受对我稍微有点亲近感。
拍摄过程中,被“扫黄打非”了
新京报:你有参考一些其他片子或报道吗?还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创作?
翟义祥:我自己有一个逻辑,就是我对生活逻辑的理解。在这种逻辑下,我没法把《马赛克少女》过分地戏剧化。那种戏剧化是超越不了生活本身的。在写剧本的时候,我也试过用戏剧化的方式去叙述这事,但最后我跨越不了我内心的坎。我和一些记者聊天,只是去感受一下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工作习惯而已。我没有做田野调查,我怕进入到那个当事人的事件之后,我自己会被带偏。所以,更多地是参考了记者推荐的一些材料。
新京报:独立制片公司“黑鳍”参与了《马赛克少女》的制作,你怎么看待“黑鳍”的参与?
翟义祥:这对于我是一个新阶段,对“黑鳍”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之前都是从中后期来介入作品的。《马赛克少女》是他们从头制片的一部作品,我们一起成长,他们也在摸索制片。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阶段。
新京报:在拍《马赛克少女》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翟义祥:没有大的困难,都是小的困难。困难主要是拍摄和技术上。比如天气和拍摄现场的协调。有一次,我们被举报后,被“扫黄打非”了。可能是拍摄干扰到居民,他们没法判断这事属于什么范畴,就举报“打非”了。
还有,为了造一些非常真实的下雨场景。我希望不是用洒水车来洒,这样太假。我们在长长的走廊里面安装了喷头来下雨,用了几百个喷头,来做出纵深感。当时基本上把那个县城的淋浴头都买光了,弄这场下雨戏就弄了好几天。
新京报:总体来说,《马赛克少女》还是一部中小成本电影,你有野心以后做更大制作的电影吗?
翟义祥:我的原则是,如果做电影的话,钱一定不是用来制作更大的场面,而是为了需要。比方说,我要做有一定的年代感的场景设计,或者是需要在某些地方花一些功夫,这就需要钱。钱就应该用到这种地方,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新京报:你自己对这个《马赛克少女》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翟义祥:我以前和人聊,比方说你给这个片子打多少分,其实只有零分和一百分,之间就没有别的分数。我肯定觉得,这部片子是我在尽了全力之后的作品,是比较满意的。如果我有过多的遗憾,那这个片子肯定是不可靠的。所以,我基本上把遗憾弥补到最低。
新京报:你选演员比如王砚辉和王传君的时候,有考虑到他们的商业因素吗?
翟义祥:没有。我找他们的时候,《我不是药神》还没有火。我见王砚辉时,他就在《我不是药神》的剧组里。当时完全不知道这片会如何。当时,王传君也在那个剧组,我不知道他俩同时在。
我们是先见了王砚辉,然后才在北京与王传君见面。其实,我们选演员的原则非常简单,对电影有帮助的、非常单纯的演员,没考虑其他因素。他们明显是实力派演员。
一开始以为只有我发现他俩的优秀,没想到好多剧组也在找他们。大家对好的标准是有共识的。
王传君、王砚辉
新京报:在演员的选择上,你觉得非职业的演员和职业演员有什么区别?
翟义祥:职业演员当然就是他们很专业,职业演员对非职业演员的认同也很重要。王传君演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些演小孩的非职业演员很刺激,能给他一些东西。王传君能认识到这一点,大家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我对非职业演员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让他们去了解生活和人物。我告诉他们:生活里面总有这样的人,总有这样的事儿。非职业演员可以不理解电影,但他们一定会对生活有观察。生活逻辑,对非职业演员非常重要。
电影的一部分,要承担调查记者的功能
新京报:你以前拍过一个短片《儿子离开北京去美国》,也是从一个新闻事件出发的。你在做电影选题时,会倾向于从新闻事件中取材吗?为什么呢?
翟义祥:有时候,新闻会给我以刺激,给我一些想法。但是,我的片子不是完全依照新闻的内容来做的。的确,新闻会给你一个新鲜的想法,或者是关于人性、关于哲学的一些想象。我希望我做的东西更当代一些,更侧重于当下。
新京报:所以,这是你用电影介入社会的一种方式吗?
翟义祥:算不上介入,应该说是一种呼应。比方说,现在大家会经常讲,新闻比戏剧更有故事。
新京报:调查记者这个工作,在中国的黄金时代可以说过去了。现在很多艺术家,包括电影人承担了一些过去调查记者的工作。当然电影是滞后的,不可能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你怎么看?
翟义祥:《儿子离开北京去美国》那部短片中,我其实想过把它扩充成一个长片。但这个难度很大,涉及了教育制度和户籍制度的问题。
电影有一部分要承载这样的社会功能,但并不是全部。在这个时代里,调查记者的位置很尴尬。他们自身就蕴含着矛盾。你们做新闻的也都知道,自己写的东西经常会发不出来。但在《马赛克少女》里面,这点会一带而过。
刻意是创作者与生俱来的一种表达意识
新京报:在你的第一部长片作品《还俗》里,用了许多象征的手法。但有些人觉得,你的象征手法太刻意了。你怎么看待刻意的问题?
翟义祥:刻意,就是创作者与生俱来的一种表达意识。带有作者性的电影,都有一种刻意的东西存在,这就是意识先行。纪录片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所有剧情片都是被设计出来的。当然,有些人的手法成熟一些,或者隐藏的方式更高明一些,就看不出那么刻意。
新京报:在《还俗》里面,你在剧作上设置了一些巧合,比如说男主角嫖娼却遇到了他的初恋,然后警察突然进来扫黄。这种巧合会不会让影片过于戏剧化?
翟义祥:我没有正式学过编剧,但这个剧本基本上按照生活流的方式去写。可能你不知道,我们生活在小县城、小镇或者乡村的人,就是会经常遇到一些熟人。这事是我从一个同学那里听来的,他的确在一个小地方做按摩时碰到了自己的高中同学,这些巧合是符合生活逻辑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还俗》对信仰的探讨?
翟义祥:《还俗》所探讨的,也算不上是信仰,它就是表达了大家在寻找依靠的状态。其实,国内的信仰基础是比较薄弱的。我在那里面讲的信仰,是非常朴素的信仰。大家只是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而寻找一个寄托,这是一种很实用性的信仰。我一直说,这不是一个宗教题材的电影,只是披着宗教的外衣,展现的是我身边的人和环境。
我是美术生,学艺术的,所以对艺术还有点小小的憧憬,但我许多的同学回了老家当老师。然后,有同学每天打电话跟我诉苦,说觉得不适应这种世俗生活,如家人催促结婚生子等,这个人最后还为此去相亲节目。创作《还俗》的时候,我本来是想写他的故事。
贾樟柯对于野生电影人来说,起到了鼓舞作用
新京报:你是学设计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电影?有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激发了你想做电影的梦想?
翟义祥:我想做电影好像是从高三开始的。我高考的时候,我就有意想考舞台美术设计或者影视美术设计之类的专业。当时我们一起画画的同学,他家里是拍婚庆录像的,淘汰的摄像机就放到我们宿舍。我们拿着那个摄像机到街上去拍东西。这是很原始拍纪录片的方式。我们到街上去采访人,然后去河边拍一些独居的老人,还有一些学校里面的突发事件。我当时很兴奋,像有了一个武器一样。
新京报:这非常有新闻记者的感觉。
翟义祥:当时,我们只是玩,觉得摄影机很像武器。每次我拿着摄像机上街,很多人就会非常警惕。那会儿,我们也会去网吧看一些电影,懵懵懂懂的,当时就对电影有兴趣。在大学阶段,我基本上就朝着将来拍电影这个方向而努力。
新京报:那有没有哪一部电影对你开启电影生涯之路影响特别深?
翟义祥:那倒没有。初中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看《卧虎藏龙》,动机是学校觉得这部片子得了“奥斯卡”,可以当作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这种组织观影都是要求写观后感的,老师觉得我对电影理解得很好,但没有体现爱国主义。那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对电影有不一样的认识。
读大学的时候,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对我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因为我受了多大的启发,而是我发现拍电影看着挺简单的。架个摄像机,演员这么生硬,大家还都觉得好。其实,《三峡好人》里的人物都很像我身边的人。
贾樟柯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让你觉得做电影是有可能的。这对我起到一个鼓舞的作用。像我这种既不是电影学院,也不是知识分子家庭或文艺世家出身的人,怎么和电影接近呢?贾樟柯告诉我,可以的。
新京报:那你在电影艺术上有受过谁的影响吗?
翟义祥:我确实找不出一个特别明显的影响我的人,但好像有一批人,比方说李沧东或贾樟柯。我做《马赛克少女》时,娄烨在工作方式上给了我不少意见,比如怎么拍摄,怎么和演员和摄影师互动什么的。我之前还有个老师叫应亮,他也教了我不少。这是一个很广泛的影响。
新京报:栗宪庭电影学校对你有什么影响?
翟义祥:应亮当时是栗宪庭电影学校的老师,他主要负责我们教学。这段经历告诉我如何低成本拍片。当然,学习的过程给我最大的启发,是如何打开思维,可以没有禁忌地去挑战许多不可能的地方,更大胆地做一些东西。比如说,拍《还俗》时,我有几万块就动手了,这在大多数电影教育系统里,是不太可能的。
新京报:你大学毕业之后,是在北京做视频吗?那段时间怎么坚持电影梦想呢?
翟义祥:那时我做过摄像,也做过剪辑,大概工作了两年多。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抱着拍电影的理想,想通过制作视频靠近电影。我从大学准备进入电影行业,之后做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电影。
我基本上通过自学:写剧本,练习剪辑,学拍摄,做美术,拍短片,唯独不会作曲。但是,每个环节我都不精,只是会而已,所以只能做导演吧。
新京报:那你学习的方式是?
翟义祥:拍短片。大学时借学校的器材,自己拍自己剪。基本上是这样,边拍边学习。
新京报:那你决定辞职去拍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
翟义祥:首先丢掉了工作,父母就不愿意。我爸妈其实有点反对,但那时候我年纪轻,无知无畏不会害怕,所以也不会考虑后果。当时经济上很有压力。我在拍《还俗》时借了钱,到现在还有一部分没还清。
“所有人都在想着开连锁店,做成海底捞。电影也一样。”
新京报:当你真的开始电影实践之后,你觉得电影和你想的一样吗?当你进入到一个相对工业化的体系里面,你所处理的东西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翟义祥:对。《还俗》和《马赛克少女》两部片子,完全是不一样的工作状态。但是,野生的魅力会一直存在。在主流观众和专业人员那里,野生就意味着不够专业。在这种情况下,利弊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我更倾向于野生原始的生命力。
比方说,你想吃西南菜,在本乡本土吃的时候,厨师的原材料也都是本土的,这当然就很像野生的电影。《还俗》和《马赛克少女》是不一样的,我在老家的时候,用本土的食材和本土的方式,做一道非常朴素的菜,肯定有它的魅力。
但是,大部分导演的第二部作品,也就是进入工业之后,就必须得考虑还要不要当初的“食材”。作料有可能还是用家乡的,可是食材也许会改变。因此,有些导演在进入工业体系之后口味会发生变化。这很像没有人想一直在小地方一直经营着小店,大部分人都在想如何开连锁店,做成“海底捞”,那么做电影也一样。
拍摄现场
新京报:那这个变化会失去一些什么吗?
翟义祥:失去的和得到的,都差不多。菜虽然是一样的,失去的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比方说,你在北京可以吃到世界各地的菜,有些馆子很努力,食材也是空运的。可是,水是北京的,最起码这点上已经变了,这当然是让人有遗憾的地方。但是,这样做至少会把一道好菜推广出去。
新京报:那你怎么去平衡工业体系和个人表达之间的矛盾?
翟义祥:我会很努力地去平衡,但会特别费劲儿。我刚才谈到的《马赛克少女》的讲述方式,事实上坚持了个人讲故事的方式,我没有做过多的妥协。
其实,在潜意识里面,或多或少会想作品是不是够私人的,要不要受干预。一些导演可能会很在意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也许不会进入到工业体系。这样的导演到现在依然存在,只是很少见了,因为这种非工业电影的生存空间基本上被彻底挤压掉了。
我刚做第一部电影时,这种电影还是有空间的。现在这样的电影,除了自己放一下,基本没有任何渠道放映。前几年,《还俗》还有一些空间可以放映,但那些放映的地方也渐渐被取消了。这是这几年明显的一个变化。
新京报:还有一些就想做纯艺术电影的作者,你觉得这还有空间和可能性吗?
翟义祥:这种坚持还是在的。但是,变化也是必然的。还有什么是坚持下来的呢?我坚持的就是个人的表达,如果电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就彻底没法玩了。
被大环境裹着往前走,是最考验年轻人的地方
新京报:你有没有一直关注的主题?
翟义祥:我更关注人性和哲学,更喜欢表达人在当下生活处境的变化。当然,肯定还要和我个人各个阶段有连接的地方。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一代年轻作者的表达和上一代电影人如娄烨等人有什么不一样?
翟义祥:上一代人在试图表达他们跟时代的关系。年轻一代还没到回溯过去的时候,还是在探索里面求生。这一代的求生欲,其实比较强。
他们那一代,有一个长期不被关注的过程,但这一代就很容易被当下大环境给裹着往前走,这是最考验年轻作者的地方。当然,这批年轻人虽然很挣扎,探索性还是在的。如果年轻人都没有一点探索精神,那就真的完蛋了。
我能感受到,当下年轻导演有两拨人,有一拨人是完全走市场的那条路,那条路也很辛苦,要按市场的模式被推着往前走;还有一种,就是想探索艺术表达的人,他们也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来争取话语空间。
创造力最好的时候,应该是在28岁之前,但这时候恰恰没有掌握任何的话语空间。当有一天掌握的时候,生理阶段和创作冲动都在慢慢萎缩,这是一个悖论。
新京报:你刚刚也说到,这一代年轻电影人的求生欲很强,这个求生欲指什么?
翟义祥: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纯粹的艺术电影、纯粹的小空间被挤压得快没了。大家在自我表达的同时,还非得在市场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可能性。在兼顾市场的同时,又要讲自己的故事,这就是要让自己的这套东西活下来之后再开始争取更大的空间,做更自我的表达,这就是求生欲。
但是,有一部分人是做产品,还有一部分人在做产品的同时努力表达自我。今年这届FIRST电影展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入围电影是非创投出来的,自己凭空做的项目已经非常少了。因为金马创投、FIRST创投,或者是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等平台孵化的项目,都在进入电影节系统。
新京报:这会对更野生的电影带来一定的阻碍吗?
翟义祥:这不是阻碍,野生的电影,一样还可以继续做。不是每部处女作拿到创投会上都能得到应得的回报,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想拍电影,那就自己弄出来。
当下的电影是一个裹挟着许多欲望的怪物
新京报: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创投”的电影时代和以前区别大吗?
翟义祥:区别当然有。我拍《还俗》的时候,就想找5万块钱都各种碰壁。哪怕当时已经拍完了,想再去找几万块钱做后期,就是没有平台愿意给我。后来,我才找到“黑鳍”,他们帮忙做了一些剪辑和后期的工作。当时,《路边野餐》也是刚拍完没有钱做后期,也是在“黑鳍”做的后期。当时大家还处在一个只是想做电影,做完之后不顾后果的阶段。
《路边野餐》剧照
但是现在,一个作者如果有了拍摄素材,可以去电影节找钱。拍得还可以的话,找钱会比以前要容易得多,相应的各方面的要求也会多一些。其实,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其实开始在写剧本阶段就可以拿着剧本闯一闯。可是,我们也必须知道,一旦上了创投环节,你的作品就不会是一个20万以内解决的作品了。进入这个创投环节之后,一个作品会很快工业化,这改变了纯手工制作的模式。
新京报:你觉得这有什么弊端吗?
翟义祥:也谈不上弊端,因为那个纯粹但是没钱的阶段,也不是特别值得怀念的。像台湾地区或者韩国,很少有像内地这种特别低成本的电影出现,大部分作者会找一些扶持金。这部分扶持金(辅导金)是一种更理性的支持,这些资助不会带着欲望进来。我们当下的电影,是一个裹挟着很多欲望的怪物。尤其是前两年电影市场那么好,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欲望都被投射进来。
新京报:但是今年的电影市场显然遇到了危机,如果没有人投资电影了,应该怎么办?
翟义祥:也许,又倒回了之前的那个阶段,但也不一定。其实很难预测,但想拍电影的人永远是有机会的。如果只是想利用一些资源做电影,也许会面临困难。想拍电影的人,永远都能找到自己的方式,不是非得依靠这些平台。
“如果这个低成本处女作没有生命力,作品就失去意义了”
新京报:你怎么看低成本的处女作?
翟义祥:我的一个直觉是,如果低成本的处女作没有生命力,作品就失去意义了。创作的第一个阶段,低成本的优势是原生的力量。正是因为成本低,甚至可以随便拿个摄影机到街上去拍,可以捕捉到很多具有生命力,更有原生状态的东西,这是低成本最大的优势。使用的是素人演员,是身边的朋友,原始的生命力或者原生状态肯定会散发。
新京报:你怎么看这几年出现的其他年轻作者?
翟义祥:其实,我这次去西宁(FIRST电影展)还是想看一些处女作,处女作甚至短片,相对更刺激。我反倒不太喜欢看更成熟一些的作品。
新京报:那这不是悖论吗?你现在正在做相对成熟的作品。
翟义祥:我只能说我在走向成熟。我喜欢看处女作,是我个人的口味。成熟导演,也许会觉得,作品上映后就和自己没关系了,但处女作的作者会很期待跟大众有对话。
新京报:对于你来说,你现在还期待大众的看法吗?
翟义祥:有一点期待,但不是很强烈。电影肯定是需要对话的,可我有时候怕找不对人对话,这种感觉很矛盾。推向市场是一个面向更广泛人群的过程,但是能够找到可以对话的同类则是有限的。因此,我不会过分地期待或者失望。
新京报:你对《马赛克少女》未来的票房有期待吗?
翟义祥:我的原则就是不给投资人亏钱,这是对投资人负责任。虽然这不是一个导演最主要考虑的问题,可也是一个应该被纳入讨论的问题。
在中国,现实主义比什么都有力量
新京报:其实,这两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还是不少的。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媒体还会有一个“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说法,不知道你怎么看?
翟义祥:这个说法不成立。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很多电影只是“现实主义”的皮毛,没有真正打开现实主义的尺度。
中国当下的情况,现实主义比什么都有力量,关键是要能拍出来。比方说《燃烧》、《寄生虫》这种片子,讨论的是阶级关系,这种题材在当下中国太丰富了,但我们拍不出这种片子。
《燃烧》剧照
新京报:现在,你有了拍摄电影的机会,比一般的年轻作者来讲要幸运一些,你会有一种文化使命感吗?
翟义祥:我不知道,我没细想过这个问题。
新京报:比如你刚才说到李沧东,他的作品是有一种知识分子式的忧虑在里面,肯定是具有一种文化使命感的。
翟义祥:我没有细想过这事,也许潜意识里面会有。我平常尽量不以这种特别宏大的目标去做事情。在这个环境里,使命感和责任心都没有用。
新京报:但是,你还在拍呀。
翟义祥:就是正常做事,其他的在尽力争取。
新京报:作为一个自由的创作者,现实的什么因素给你的压力最大?资金的问题压力大吗?
翟义祥:这几年资金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只要有才华。在正常的市场机制中,钱永远都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制度和人本身展开的那种张力。
像《切尔诺贝利》这种片子,成本高,费功夫,但只有几集。必须有成熟的市场和制度配合,主创才这么自信地去做作品。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是给不了这样的自信的。假如我要做一部好的现实主义作品,一部有人文关怀的电影,既担心资本,又害怕制度,那我就没办法拍,这是我面临最难的地方。
HBO出品美剧《切尔诺贝利》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思考的?当现实遭遇困境之后,是否会更强烈?
翟义祥:以前我就会考虑这些问题,但没有这么深入地去想,这毕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必然要去做一定的妥协,或者必然去选择。但还是要去争取,一定不能放弃,要尽量让自己保持一个全力争取的状态。
新京报:你刚才讲钱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你怎么看待之前对胡波的那些报道?年轻电影人被塑造成贫困艺术家。
翟义祥:确实,拍电影也可能很穷。胡波在拒绝更大的资本,保持了自己作品的纯粹性,结果还是会遇到一样的不自由的困境,这会让人很失望。一个作者坚持可以什么都不要,只要作品,却发现依然做不到。做电影,就是要面对这方面的欲望,这和写作不一样。
新京报:那么,在拍《马赛克少女》前后,你会不会焦虑?
翟义祥:拍摄前,其实不会有焦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还是挺充实的。反而拍摄完成后会有焦虑,我特别理解胡波,事实上拍电影就像生孩子。怀了好几个月的孩子出生之后,那种产后抑郁才是最大的心理问题,会感到空虚和失落。我在拍完《马赛克少女》之后,有好几个月不适的感觉。
也许很像你们记者彻夜写了一个星期的稿子,好不容易完成后那段暂时没有新工作的阶段。
新京报:那你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翟义祥:我自我调节能力还好,平常会和朋友喝喝酒聊聊天,也会找点事做。
作者:余雅琴 徐悦东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