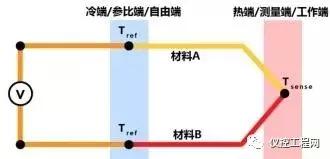陈季冰/文
最近,很多生活在英国的朋友在朋友圈和微信群发了许多伦敦庆祝伊丽莎白二世登基70周年“白金禧年”(PlatinumJubilee)的图片和视频。
身在伦敦的朋友们告诉我,这个夏天,不管你关心还是不关心,关于“白金禧年”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和活动预告每时每刻都会涌入你的视线和耳际。除了政府主办的宴会、演出、游行、展览等活动,民间也有许多自发的庆祝活动,甚至英国各地的华人圈子都是喜气洋洋的……可以说是一次举国参与的狂欢节。
实际上,伊丽莎白二世登上英国王位的法定日子是1952年2月6日,也就是她的父亲乔治六世逝世当天,后于1953年6月2日加冕。英国政府在6月2日至5日安排了4天公共假日,并举行各种活动正式庆祝女王登基70周年。而在今年2月5日那天,伊丽莎白二世只是简单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感谢70年来各界对她的忠诚与支持,也再次向英国社会重申了自己将要终身奉献于王室和国家的誓言。
一方面,很多英国民众的确是在向这位96岁高龄的女王表达他们真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也把这次“白金禧年”庆贺当作英国彻底解除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回归正常生活的一个开张仪式。
今年2月,女王本人也曾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令大家提心吊胆了好一阵。所幸她吉人自有天相,近百岁高龄之躯,只是有一些感冒症状,一周就痊愈了。这件事情本身也极大地缓解了英国对奥密克戎病毒的紧张情绪,加速了英国的全面开放。
不过,当下全世界毕竟还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所以今次的庆典还是缩水了不少。回想10年前女王登基60周年的庆祝活动,那可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盛宴。其中,2012年5月18日在伦敦城西面的温莎城堡举行的午宴,云集了当今世界一大半的君主或他们的代表,几乎就是一次“全球王室大派对”。
2011年5月初,我一位常年生活在英国的大学同学回上海度假。那时的英国刚刚经历了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正为选举制度改革的全民公投而陷入激烈辩论。
聊起政治,我问了老同学一个长久以来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既然议员主要是世袭和任命的英国国会上院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权力,为什么还要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同学不假思索但却非常坚定地回答:“因为上院是大不列颠悠久传统的象征。”的确,从某种意义是说,一部英国千年历史,就是一本讲述“对传统的尊重如何促进了现代化”的教科书。
当然,与上院相比,更能象征大英帝国令人骄傲的伟大往昔的是王室。就像伊丽莎白二世在议会发表登基60周年演说时曾说的:“历史长河犹如一条纽带,连通王室和议会。”
一
1952年2月6日清晨,25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与高大英俊的丈夫菲利普在肯尼亚度假时接到一个来自伦敦的电话:她的父亲乔治六世已经去世,她现在是这个庞大帝国的女王了。
以后70年的历程证明,虽然她的这份工作是世袭的,但这位当时的“世界甜心”似乎生来就是成为统治者的料。
伊丽莎白即位的时候,正是邱吉尔、戴高乐、斯大林、杜鲁门和毛泽东……这些旷世巨人们主导的时代。当时的世界,还在从二战的硝烟和废墟中艰难地复苏。而她父亲所统治的帝国版图正在四分五裂、急速缩小——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脱离英国的统治。作为一个明智的现实主义者,女王欣然接受了这一不可阻挡的转变。
表面上看,女王的一生平淡无奇,似乎没有什么为人记忆深刻的建树。然而,正如许多观察者注意到的,她在位时间之长,本身就是一项难以置信的成就。早在10多年前,她的在位时间已经超过了亨利三世(1216年至1272年在位)和爱德华三世(1327年至1377年在位);而到2015年,她已经超越维多利亚女王(1837年至1901年在位),成为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而载入史册。
自从1953年6月2日正式加冕以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已经与14位英国首相和14位美国总统共事过。从温斯顿·丘吉尔开始,她近乎每周接受一次首相的拜见。女王和首相们都没有透露过具体的谈话内容,但许多首相——如毁誉参半的前工党首相托尼·布莱尔——都谈到了她的智慧:她时而直言不讳,时而幽默俏皮,有时甚至有些恶作剧……
对于已经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人类君主制度而言,刚刚过去的20世纪可谓流年不利,世界上那些古老而伟大帝国以及它们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们——从奥匈帝国到沙皇俄国,从满清皇帝到奥斯曼苏丹——一个接一个被革命的炮火扫入斑驳史书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已经从容走过了将近300年的英国温莎王朝 (HouseofWindsor)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带领下,不仅安然度过了席卷全球的君主制危机与一系列社会动荡,前几年,反而还颇有绽放出“第二春”的味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当支持君主制的英国人唱到《天佑女王》(GodSavetheQueen,英国国歌)中“治国家,王运长”(Longtoreignoverus)这句歌词时,很可能比以往更发自内心。
这一切,在君权神授的政治合法性已经被社会契约取代的现代社会,几乎全部系于女王一身的人格魅力。她凭借与生俱来的沉着、冷静、优雅和高贵,经受了一次次的考验,赢得了人民的爱戴。
当然,女王和王室也曾经遭遇过重大危机。在少数情况下,女王会严重误判公众的情绪。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出现在1997年,备受民众喜爱的戴安娜王妃因车祸去世后的最初一周,女王过于理性谨慎的处事方式被视作冷酷无情。当时,她留在苏格兰高地度假,只签发了一项简短声明而没有立刻返回伦敦去安慰数以百万计的哀悼者,因而遭到严厉批评。不过,后来她发表了充满同情心的电视讲话,同白金汉宫外面悲痛的妇女对话,并向葬礼队列中的戴安娜灵柩鞠躬……这一切又为她重新赢回了人心。
与半个多世纪前相比,今天的英国王室正在朝着更富时代感、现代化的方向蜕变,这可以从它本身近年来的一系列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变革中窥见一斑。
2011年5月17日,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历史性地访问爱尔兰——那片被英国人称为“最遥远的邻居”的土地,成为自该国独立后第一位来访的英国元首。上一次是在整整100年前——1911年,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也就是女王的祖父——最后一次以爱尔兰国王身份访问该国。此后,再也没有英国国王踏足过这个历史上与英国纠缠难解并充满爱恨情仇的国家。
2011年10月底,于澳大利亚珀斯召开的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同意,废除英国王位继承男性优先及与罗马天主教徒通婚者不得继承王位的禁令。这些王室继承传统要追溯16世纪的另一位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并被1668年和1700年的继承法确认。
二
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家兼作家沃尔特·白芝浩 (WalterBagehot)曾写道:“王室会适时地用一些美妙愉悦的事件为政治增添一些甜蜜感。”
许多人至今还对2011年4月29日威廉王子那场盛大的婚礼津津乐道。与后来哈里王子与美国女星梅根·马克尔那令人议论纷纷的婚姻不同之处在于,威廉将在未来某一天继承英国王位。这场婚礼除了在英国和全球时尚界掀起了一阵“凯特效应”外,还被另一些人寄予了政治经济上的厚望。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宿命,威廉王子的婚礼也同他的祖母伊丽莎白二世与父亲查尔斯王子的婚礼一样,都发生在历史性的经济衰退和财政紧缩年份。这使得勒紧裤腰带的国民们,对举行铺张的婚礼以及庆典所耗费用是否恰当提出了许多尖锐的疑问和批评。政府希望借王室大婚的盛事提振内外需并鼓舞民心,给低迷的经济注入活力;而普通的民众更希望借婚事来对金融危机阴影下黯淡悲惨的世界“冲喜”,这种情绪甚至扩散到了英国以外的世界各地。
对“保皇主义者”来说,威廉王子与凯特·米德尔顿是梦寐以求的一对——他们富有魅力、讨人喜欢,举止在国民眼里中规中矩。查尔斯和黛安娜婚姻的失败以及一部分王室成员飞扬跋扈的做派及重重丑闻打击了王室作为家庭典范的地位,许多英国人认为威廉与凯特必须恢复20年来王室丧失的某些尊严。因此,他们的婚姻——无论成功或失败——恐怕都将对君主制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但让一对年轻夫妇来担负起这一命运,这顶王冠似乎实在太沉重了。
好在年轻的剑桥公爵和剑桥公爵夫人(这是威廉王子和凯特·米德尔顿婚后得到的封号)迄今为止做得不错。OpiniumResearch网站在他们结婚一周年之际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的英国人认为,这场婚礼让王室变得更讨人喜欢。
在启蒙以后的现代世界,要说反对君主制,显然有数不清的理由——通常都比支持君主制的理由要有力得多。
2011年早些时候,瑞典王储维多利亚公主嫁给她的私人健身教练丹尼尔,婚礼花费了瑞典纳税人1140万美元,在瑞典国内引发争议以及对君主制前途的辩论。说老实话,维多利亚能否从其父──现年74岁的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那里顺利继承王位,实在是个未知数,因为瑞典公众对王室的支持率正缓慢但持续的下降。
1999年,澳大利亚也曾就该国“是否脱离英国、改制为独立的共和国”举行过全国公投,结果很勉强地遭到否决。
由于国王已经不再掌握任何实际权力,共和派借以攻击君主制的最有力的理由就在于王室享有的特权,尤其是:它有什么理由得到纳税人的供养?然而,“保皇主义者”却说,女王和王室就像是英国的一个全球知名商标(事实上这可能是英国最知名的商标了),对外国游客极具吸引力。因此,纳税人的这点钱花得很值得。
与经济账相比更重要的,正如本文开头时我的那位同学所说的:国王和王室代表了一种值得荣耀的英国传统。英国《经济学人》前任主编Emmott曾经写道:人们对王室的感情就像对待一座他们崇敬的历史建筑,一旦坍塌必然感到无比惋惜。因此,君主制是英国人借以进行身份认同和维系爱国主义情感的纽带。我们几乎可以断言,如果英国废黜了国王,那么随之而来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英联邦的解体。对许多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民众来说,约翰逊首相不过是同拜登总统一样的普通外国领导人,但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廉王子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陛下”和“殿下”。因此,如果国王和王室都不复存在了,这些远在万里之遥的国家不会觉得再有任何理由承认与英国的特殊关系。
三
在当今世界,国王(女王)、王子(公主),乃至总督们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里。不过我们很少在真正讨论国家大事的严肃场合看到他们,他们的身影频繁出现在诸如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这样轻松而热闹的聚会上。当然,他们日常最平凡的工作也是慈善、环保、妇女儿童权益等社会公益事业。
说起来其实也很好解释,一方面,在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女王)虽然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但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或傀儡,毫无实际权力。而在另一方面,世博会也好,世界杯也好,虽然规模盛大,甚至举世瞩目,但说到底都不是什么有太大严肃意义的政经大事。这种时候,出于对世博会主办国的尊重和礼貌,出于对在赛场上为国拼搏的球员的激励,作为礼仪上规格崇高但又不实际参与行政的国家元首,平日里清闲低调的王室成员代表国家出一下场,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君主制,是古代政治留给现代世界的一条最显眼的尾巴。按照古代政治理念,君权是神授的(在中国则是“上天”授予的),所以庄严的英国国歌是这么唱的:上帝保佑女王……而根据启蒙以后的现代政治哲学,国家是人民订立的一份契约,因此不管是总统、主席还是总理,他们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
然而,有一个事实令人费解:经过数百年来的社会进步,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君主立宪国家早已是名副其实的民主国家,可为什么它们的君主制总体看来依然稳固?虽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一直有一些人主张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但似乎大多数人对这项“进步事业”并无太高热情。
将近20年前,我在瑞典学习生活过两个月。我也曾拿这个问题询问过同为君主制的瑞典的朋友们,得到的回答不外乎以下几条:第一,一般老百姓不想折腾,他们觉得维持现状没什么不好;第二,超越了党派利益的王室的人格力量在某些关键时刻能够发挥重大作用。这点在比利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要不是比利时有一位深得民众爱戴的国王,这个西欧的富裕小国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分裂为说荷兰语的佛莱芒和说法语区的瓦龙两个国家。而在亚洲,泰国前国王普密蓬在历史上曾经凭借个人影响力化解过多次军事政变引发的严重政治危机。
说实话,在我看来,这些解释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而且,事实上,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它也许能够十分幸运地造福国家,但历史书里更多的却是人治留下的教训。人生而为圣贤还是魔鬼,是十分难料的。西方国家过去几百年来通过不断的改良和革命发展出来的今天这样一套复杂的政治制衡机制,不正是为了防止不受限制的个人权力为祸人间吗?
我相信,在现代民主宪政制度之下,人民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陛下”,并不是对他(她)有什么现实的期待,而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寄托:即便是在这个祛魅已久的后启蒙时代,政治(或者更宽泛地看,其实也就是世俗社会生活)仍然需要保留一份神秘的神圣性。为什么上帝会去保佑一位国王或女王,而不会去关心一位总统或总理?因为国王或女王的身份、地位和权杖都是上帝赐予的,与我们普通民众毫无关系。而总统或总理,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而且,恰恰是我们让他们成为他们的。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曲折隐秘的社会心理,我们经常看到民主国家的媒体肆无忌惮地攻击漫骂民选的总统、总理和议会,但我们很少看到他们会以侮辱性的粗鲁语言加诸王室身上。在这些国家,普通民众面对总统时仅仅是表示一下必要的尊重和礼貌;但他们面对王室时的态度,除了尊重和礼貌,却又平添了几份微妙的虔敬,仿佛他们面对的是耶稣基督亲自赐福过的圣物。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与总统、总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我们与国王和王后却注定是不平等的。吊诡的是,在这个一切追求平等的年代,正是这份不平,维系着我们内心深处强烈渴望着的某种神圣情感。这种情感实际上存在于生活的许多方面,只是我们平时很容易忽略罢了。当我们形容一个人在某个领域内的成就达到了凡人不可企及的卓越地位时,我们会说他(她)是“球王”、“歌后”、“影帝”……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打算把他(她)形容为“足球场上的主席”、“歌唱界第一夫人”、“电影总统”……难道主席和总统的权力不比国王和王后大得多吗?但很遗憾,它们仍然不过是一份职业而已。国王和王后不是培养和训练(还有竞争)出来的,他们是上天选中的。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在现代社会,这种神圣性是极其脆弱的,一旦打破了,就绝没有可能再加以恢复。那些君主立宪国家的国民们也许永远都会用一种神圣与神秘夹杂的情感仰视着他们的王室,这只是因为这些国王或女王的血统里流淌着古老而高贵的基因,但他们绝不会接受一个凭借着现实政治权力而自我加冕的冒牌君主——辛亥革命的炮火剥夺的,不仅仅是爱新觉罗氏的“天命”,它已经一劳永逸地勾销了一切天命。可怜和可悲的袁世凯却不懂得这个道理。
四
也因为这个缘故,君主制就像一件精美但脆弱的景德镇瓷器,一旦打碎便永无可能再修补。英国王室传记作家RobertLacey一针见血地说:与制度永远高于个人的民主共和制相反,君主制是否为人接受,完全取决于身居王位的人。“英国曾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在克伦威尔统治下,英国曾经历了11年的共和制。我们可以再次这么做。”当然,这显然不是指把国王再一次送上断头台,而是指用和平的办法将他(她)赶下王位。
因此,英国人心知肚明,伊莉莎白二世女王去世之日,即是共和派卷土重来之时。但眼下,他们最希望的便是看起来身体健康的女王能够尽早就王位继承事宜作出决断。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民意调查结果均表明,绝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与查尔斯王储——那个弃戴安娜而娶卡米拉的令人讨厌的男人——相比,身为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的威廉王子将是一个更好的国王。不过这不仅要得到英国议会专门立法通过,还需要获得女王本人的批准。
整整1/4个世纪前,被誉为“英格兰玫瑰”的戴安娜突然去世时,女王经过短暂迟疑后曾经迅速作出了顺应民心之举。今天,在她已经度过70周年国王生涯以后,能否再度大胆抛开惯例,开启一段新的王朝故事?
历史长河不仅是一条纽带,更是一部推陈出新的永动机。如同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终有衰败的一天一样,世界上最古老的温莎王朝也难免有走向坟墓的时刻。但在人类第一个现代共和国(美国)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去已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它的幸存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奇迹。
2015年3月初,威廉王子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上海,他到访了一所中学——上海市南洋中学。这是一所以开展足球运动而闻名的学校,凑巧,它是我的中学母校。
说起来,南洋中学在今天上海的教学质量和高考排名榜上只能说勉强跻身中上水平,远谈不上是一所出众的学校。不过它倒是颇有一些令我自豪的历史记录:它成立于1896年,是有正式记载的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西式现代中学校。在它之前的所有在中国土地上的现代学校都是洋人办的,它校门上的四个大字是蔡元培先生亲笔题写,蒋介石也曾为它的某一年校庆专门题过词,这里还曾走出过文坛泰斗巴金和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正是他把尚未公布的“二十一条”透露给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从而令日本帝国主义蚕食中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暴露无余)……
7年前那个初春的下午,当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特地早早地守候在威廉王子必经的马路边上,目送着王子的车队浩浩荡荡驶过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就是一件事情:再过二三十年,当我自己已是一个垂暮老人时,我可以向很多人吹嘘,现在的这位英国国王曾经专门到过我的中学母校!
现在离那一时刻还有很长时间,中间也许还会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变故。但我诚挚地希望,自己的这个心愿不会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