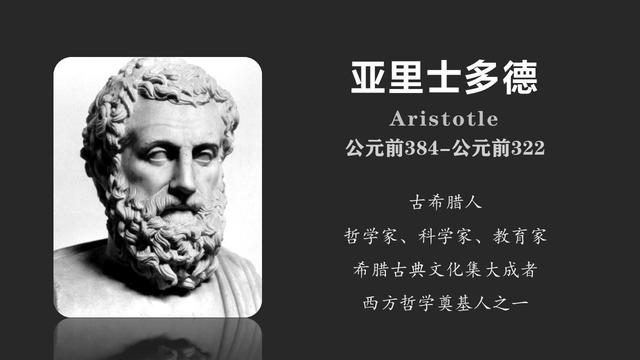在苗族人心里,苗绣是日常必需,也几乎是每个苗族姑娘一生的使命。刘绣发7岁时就开始跟着外婆和妈妈习绣,弟弟出生后,她背着弟弟接着绣。施洞地区的苗绣一般先在纸上剪出图案,再贴在底布上,把剪纸缝进线里。刘绣发白天绣花,晚上剪纸,日日夜夜绣花唱歌,过于魔怔的样子被妈妈骂成"二百五"。
她的剪纸都是随兴创作,连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游记》也成了她的素材,取经的师徒四人进了她的绣片里,也帮她拿了奖,卖了钱。"老鼠取亲"的故事更是被剪成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纸样。她既卖绣品给慕名而来的外乡人,也卖纸样给本地只会绣花不会剪样的姑娘们。
施洞的破线绣是苗绣里的楚翘,如今在收藏界,一件完整的绣衣动辄十万元以上。
之所以被称为"破线"绣,是因为这种绣法首先要将一根普通绣线手工均分成8或16股更细的线,分好的彩线再分别穿上针,线随针穿过皂角叶子,皂角液可以使彩线变得平顺、挺括、亮泽,也不易再沾色。破线绣的工艺如此讲究,绣出来的成品效果华贵、雅致,也非常费时。完成一套精美的破线绣嫁衣,可能耗时4-5年时间。
摄影:谷佳骏
"不识字才是绣娘"
每一个绣娘的背后,都是上一代的悉心教授,和自己数年如一日枯坐耐得住寂寞的磨练。当然,也少不了上古传说的给养与放飞的想象力。
苗绣没有绣谱,见山画山、见水绣水、绘龙画鸟,上古神话与天地万物都被有心人记下来,以图案的形式绣在衣服上。因此,苗绣被现代人视为"道法自然"的哲学,也被称为"写在衣服上的史书"。
每当有人拿着绣片寻问这些图案的含意,刘绣发都讲得眉开眼笑。
她给我们拿来一幅绣片,说要摆个故事给我们听。长条形小绣片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图案是对称的,中间一对鸡,两侧分列一对小儿、羊、鸡和鱼。
她按着从外婆那儿听来的故事"摆"起来:"这说的是,公鸡打鸣,天就亮了,人起床后,家里来了亲戚,要杀羊宰鸡招待客人。羊和鸡虽然是给人吃的,但它们也不想死啊,就和人商量,捞江里的鱼来宰了吃,鱼觉得很冤,也很痛苦,死了也不肯闭上眼。"
故事讲完,刘绣发自己啧啧感叹:"你听这故事,讲的意思可深了!"
摄影:陈沛亮
苗族人没有本族文字,但是他们的思考始终上达天意:人从哪里来的?宇宙万物与人是什么关系?祖宗们有过思考,也有过找寻,他们把答案绣在了绣片上,由母亲传给女儿,将创世神话和传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苗族共有一百多个支系,服饰也有一千多种,每个支系的苗衣都有自己独特的制衣技艺和风格。
刘绣发有一幅获奖作品叫《蝴蝶妈妈和姬宇鸟》,她又摆故事给我们听:"以前啊,人类只能生一个孩子,觉得太孤单了,就去求蝴蝶妈妈,给她唱歌,给她织美丽的翅膀,就这样打动了蝴蝶妈妈,给了人12个蛋,从此人类就能生好多好多的孩子……"
刘绣发有两个女儿,二女儿承了父业做医生,大女儿和她一起经营刺绣店。店虽小,一楼是成品展示,二楼却尽是她淘来的老绣衣。走南闯北见识广博的她,把二楼布置得非常规整、系统,像个小型的苗绣博物馆。作为台江县级苗绣非遗传承人和"百佳绣娘",她应邀去过澳大利亚、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马来西亚等许多国家。她还在北京潘家园摆过摊,不识字却精明,入耳的故事都被她记住,帐目也全在心算。
刘绣发是她这一系的第五代,苗名音读"无求",追溯至"蝴蝶妈妈"那时叫"无鲁"。外婆和妈妈绣了一辈子,天天摆故事给她听,却不支持她天天绣,她们觉得识字学习要紧,绣东西"没用"。她15岁那年,背着弟弟边绣花边唱歌,唱来了一个老外,跟到家上了楼,看了她满屋子的绣品,说"你有多少我都要"。那一次,她赚了五万块,她挺起胸脯对外婆、妈妈说,绣东西"有用"。
她也悟明白了关于苗绣的一件事——"我不识字才是绣娘"。
歌没了,苗绣的魂就没了
榕江县摆贝苗寨的潘老拉也不识字,甚至不怎么会说普通话。她是寨子里数一数二的绣娘,而且人又有耐心,许多年轻姑娘都来找她学习刺绣,最后连她的丈夫也被收归门下。
摆贝苗寨依山而建,是月亮山麓最古老的苗寨之一,整个寨子的吊脚楼错落绵延,被雾气笼罩时,有一种世外秘境的感觉。摆贝的杨姓和潘姓居多,寨子的杨姓祖先杨老老因骁勇善战反抗清廷被尊为"苗王"。
百鸟衣和牯葬节,让这个大山深处的苗寨闻名于外。
在摆贝苗族的信仰里,鸟是上古图腾,"百鸟衣"真正的名字应该叫"牯藏服",是牯藏节时穿的盛装。目前主要流传于黔东南的丹寨县、雷山县、榕江县、三都县等20多个自然村寨。牯藏节是苗寨最隆重的祭祀活动,每十三年一次,寨子里无论男女都要穿上百鸟衣,家家都要挂出或蜡染或织绵的长幡,以祭祀祖先。
摄影:陈沛亮
到摆贝寨寻找百鸟衣的当晚,我们赶上了一个男孩出生11天的宴席,此地风俗是在新生儿的第11日和百日开宴请客。晚宴是流水宴,吃一拨走一拨,众人围着火,拿两个三角长条矮凳搭成四边形当餐桌。简陋的屋子里大大小小组了五桌,坐的都是女人、老人和小孩。年长的大多穿着当地苗服,头巾和绑腿都有自己做的刺绣,年轻人则大多一身的现代装束。
吃了一肚子的辣椒蘸水白煮肉后,我们的胃有点吃不消,以至于在潘老拉家见到一箱子的百鸟衣时被惊得直打嗝。几乎所有的饱满亮色都被使用在整件衣服上,且密密落满了各种图案的鸟,看起来有着原始部落的朴拙和神秘感,裙脚排列一束束的羽毛,像是附着了无数飘飘欲飞的魂灵。如此艳丽不羁,如此任性多姿!
百鸟衣工艺细密复杂,其中最耗时难得的是整件绣衣的蚕丝底板。要由蚕在木板上面沿着布好的经纬线一层一层地吐丝,直到吐出一张厚实而绵密的丝板,然后染出颜色,再一针一脚在上面开始绣。
摄影:陈沛亮
要养护蚕的生命、要指挥布局、还要一点点清理蚕粪……要花费的耐心可想而知。一件百鸟衣,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
潘老拉在电灯尚未普及的岁月里,同她的妈妈、妈妈的妈妈一样,在堂后厨房里,砍一根松木,削成一截一截,放进油灯里点燃,就着这样微弱的光照,唱着歌,在蚕丝板上日复一日地绣。
寨子里上了年纪的绣娘几乎都不识字的。少女和少妇的生活总归有些辛劳和枯燥,绣东西就成了她们的闺阁之趣。
摄影:陈沛亮
绣片里的神话故事,也是她们想象力的源泉。
"公老路过山坡上去砍了一根柴,柴里面有10个蛋:1个蛋变成了白画眉;2个蛋变成了凤凰鸡;3个蛋变成了条龙王;4个蛋变成了蜈蚣;5个蛋变成了龙蛇;6个蛋变成了鹅龙;7个蛋变成了青蛙;8个蛋变成了蝴蝶王;9个蛋变成了水牛龙;10个蛋变成山羊王。一群动物团结在一起来跳歌舞,……"
不识字的潘老拉边绣边唱,这些歌都是外婆和妈妈教的,歌更像是被吟诵出来的,一边缓解绣东西的疲劳,也成了帮助绣娘们绘制图案的"绣谱"。
歌没了,苗绣的魂就没了。
没有文字,只有口传,一代一代的传。可是没有多少年轻人肯坐下来学着绣东西了。又能传给谁呢?
潘老拉的丈夫上过学,经父母介绍结婚,婚后外出打工,给人盖房子,太辛苦,潘老拉便教他也一起绣东西,如今也是苗寨里的"男绣娘"。潘老拉绣的时候唱歌,他便一句一句地翻译了记下来,把这"无字天书"摘写在了纸上。他说:"也不是为了传给别人,就是觉得应该要写下来"。
绣品里代代相传的爱
2018年的跨年夜,正好是老屯村苗年的前一天。不同苗寨过苗年的时间不一,外人刚巧碰上,也得看运气。
运气颇好的我们赶上了姚祖英家的苗家年夜饭。姚祖英的表姐张文英在台江县有一家刺绣合作社,把不少周边地区的绣娘们组织起来一起做绣品,她们的很多作品都跟随着时尚设计品牌走向了世界。
姚祖英和她的姐妹们都是刺绣里手,获得过各种级别的奖项。一家人酒足饭饱歌尽之后,她把压箱底的绣衣一件件取出,看着这些保存完好的衣服和绣片,她上高中的小女儿比我们还兴奋。女儿把小时候穿过的衣服又套在身上,肥瘦还行,但是袖子短了很多,这情境让大家都哈哈大笑。
小姑娘平时要上学,没跟妈妈好好学过刺绣。我问她,"将来你的女儿没有妈妈做嫁衣,可怎么办?"她理所当然地回答:"我妈给我绣了那么多,都可以传下去啊!"
每一个女孩,都希望得到来自母亲的祝福与爱。苗绣,不仅仅是一门手技,更是一种表达,一种抚慰。在父系社会,女人有女人的价值,而且是得到社群、家族和男人的认可的价值,她们会保存母亲为自己做的嫁衣,也会为自己的女儿做嫁衣。一件物品,表达着不需要文字来传达的情感。
摄影:谷佳骏
苗绣之美,初初觉得太过于直白热烈,只有近距离时,才会不自觉地被它的神秘和体贴而吸引,仿佛那图案里藏着自己的身世与来处,而那种丝线的细密质感,又仿佛有着母亲们抚摸过的温度。
在刘绣发和姚祖英的绣品店里,我们都听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拥有一件珍贵绣衣的老婆婆,膝下无后,百年之后,便以嫁衣陪葬,精美绝伦的绣衣也永远在人间消失了。
听起来孤绝又缠绵,让人潸然泪下。
文字根据线上传播方式对原作有部分删改。
撰文:语鸿。内容来自:《地道风物.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