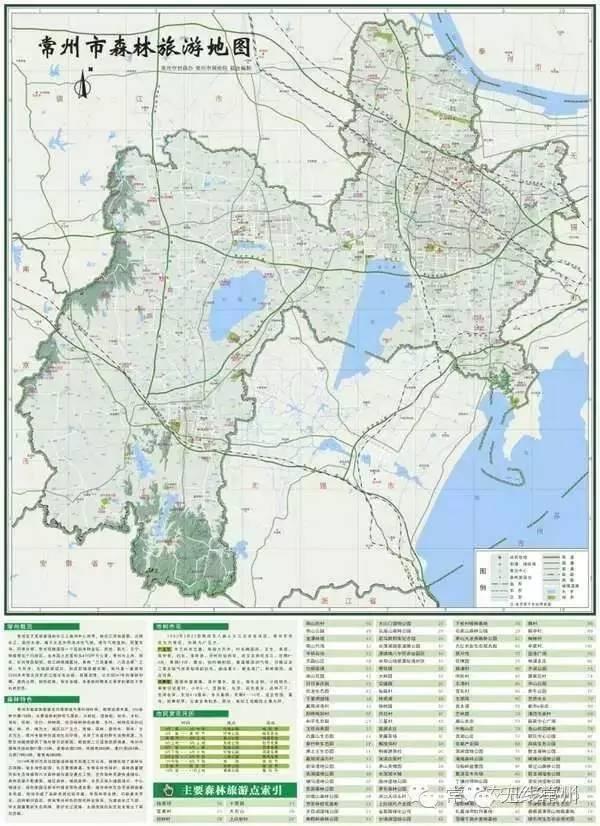一
一个客人在金子身上纠缠的时候,金子的电话“吱吱”震动了。金子有两个电话,一个是业务联系的,红色的;另一个是跟家里联系的,银白色的。银白色的手机嗡嗡地震动着,在床边的茶几上,几乎要跳起来。那个手机就像那个客人。金子请求地说:“我接一个电话行吗?”客人很扫兴地说:“他妈的,偏偏这个时候来电话。”金子媚笑着,还是伸手拿过手机。她知道是妹妹二嫚打来的。竟然在这个时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姐,这个月,你怎么没往卡里打钱啊?咱妈老病又犯了,现在在医院里。医院让交二千块钱的押金,我……”
“我没打钱吗?我记得我好像打了,要不就是我忘了,姐马上就去银行。你别着急啊,好好地照顾咱妈。”金子说完就想起来,可是那个客人压在她的身上。她说:“大哥,家里出了点事,改天我一定好好服侍你……”客人不情愿地用眼睛剜了金子一眼,骂了一句:“他妈的,今天真扫兴,连五分钟都不能等了吗?我就要……”金子说:“不能。”金子伸手温柔地摸了男人的脸一下。男人百米冲刺地弄了几下,还是完成了。这让金子很厌恶,金子愤怒地推开了男人,问:“你的手牌多少号?”男人疲惫地伸过来,金子看了一眼,从房间里冲了出来。她跟服务台说了一声,就从华都走出来了。
城市的八月还看不出什么,只是白天比较热,“秋老虎”让人不敢出门。晚上,秋风起,瑟瑟的冷。金子从华都洗浴中心出来,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瑟瑟的风,瑟瑟的冷包围了她的身体。她一激灵,哆嗦了一下,连忙拽了拽敞开的衣襟。她穿了一件半截的裘皮大衣,里面是精致的胸罩,再就什么都没有了。下身是一件超短裙,两腿上裹着黑色的丝袜。在灯光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从台阶上走下来的模特。她长得很像电影演员姜宏波。风吹着路边的一棵树,那风声中,金子感觉到了秋天。那声音就是秋天的声音。尽管来这座城市快十年了,但她仍记得秋天的声音,风的声音。本来,她打算这几天就回去的。具体说,还要两天,就是她的生理期了。她要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回去看看。中秋节前几天,她还特意买了好利来的月饼,给家里寄了回去,还打电话跟妹妹说,过几天就回去。没想到,现在,母亲突然病了。
电话再一次响了。
“姐,你钱什么时候能到啊?这么晚了,银行还能开吗?”
“二嫚,这边有二十四小时营业的银行,就是不知道老家那边有没有。你跟医院说说,明天一定给他们交上钱,叫他们先给咱妈用药。”
二嫚在电话的另一端哭了。
“人家说了,这是制度,不交钱,就不给用药。”
“妈的,什么狗屁制度了,人要死了,还要他们医院干什么?二嫚,你别哭,再想想办法?”
“姐,我没有办法。”二嫚绝望地说。
金子想想,也是,除了钱,还能有什么办法。再说了,对一个初中女生来说,能有什么办法。
“妈呢?”
“妈躺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呢?”
“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太好,喘得厉害。”
“能挺到明天早上吗?”
“不知道,这次看上去比以前都严重。”
金子仿佛听到了母亲喘息的声音,像电锯在割着她的心。她在心里埋怨自己,怎么就忘了往卡里打钱了呢?
秋风瑟瑟的冷。
金子在电话里安慰二嫚,叫她好好照顾母亲,钱明天早上,一定会到的。她撂了电话,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她租住的楼房。她拿出钥匙打开门,冲进屋里,在床下翻找着她的卡。当她打开藏卡的点心盒的时候,她傻眼了,一股血嗡地冲上了脑门,只觉得天旋地转。她掏出点心盒里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了那张卡。她浑身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怀抱着那个点心盒,里面空空的,只存在空气。她喃喃着:“卡呢?卡呢?”她从地上站起来,翻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还是没有。她甚至撒开床上的一个布娃娃,掏出里面的棉絮,也没有找到。她气急败坏地把布娃娃扔到地上,狠狠地用脚踩了几下。“怪了?难道那张卡长膀了吗?不可能,一定是成光干的,狗日的,没良心的,手竟然伸到老娘头上了,有你好看……”尽管,她这么怀疑成光,但她还是有点不能相信是成光干的。说不定是小偷。要不就是……她的眼睛看了书架上的一堆书,她眼睛一亮,飞奔过去,一本本地翻着。一个小姐竟然有这么大一个豪华的书架,看了就叫人匪夷所思。而且,书架上堆满了世界的经典名著,还有大学的教科书。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以前,那些书可能是金子的精神食粮,现在这个时刻,不是了,而是一堆可能藏着她的银行卡的纸。或者说是废纸。“哗哗”的翻动的纸页,像巴掌似的扇着她的脸。翻遍了,每一本书,没有。这就是结果。那些书被她狼藉的扔在地上。她急得几乎快要哭了。她心疼,像被刀子剜了一下似的。那卡里,可是她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现在,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一丝希望了。她只能再一次怀疑成光了。只有成光,是唯一的可能。她打成光的手机,关机。她骂骂咧咧的,就仿佛一扇希望的门被堵死了。她的心里虚了一大块,没着没落的。那些钱就是她心里的秤砣,现在,突然,没了,也就是说秤砣不见了,本来有秤砣的时候,沉甸甸的,现在没了,整个人也变得轻飘飘的,像没有了根基的浮萍,像秋天的蒲公英,像天上的风筝,被风吹着,飘了起来。浑身的骨头,内脏,还有一腔的血液,皮肉,都变成了纸一样的轻,轻得叫人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希望的亮光,就仿佛一间点着灯的房间,突然,灯熄了,灭了,满屋子的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那一刻,金子感觉她的眼睛瞎了,心瞎了,不辨东南西北了。金子只觉得嗓子眼发热,一口血喷了出来,喷在墙上,红色的,模糊成一个拳头的形状。金子晃了晃,手扶着墙,身体的感觉就像是第一次做人流似的,除了疼,还是疼,剧烈的,缓慢的,丝丝拉拉的疼。过了很长时间,她才缓过来,但嘴里魔魔怔怔地嘟囔着:“不能丢,不能丢,不能丢,不能丢……”。她在屋子里转着,左转,右转,东看,西看,脚下踩着那些世界名著,踩着那个布娃娃,踩着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她嘴里却没有停过嘟囔着那句“不能丢”,就像念经似的。如果给她剃个光头,再穿一身尼姑的衣裳,你们一定以为她在念经,超度什么似的。
金子面无血色,像一个女鬼,在屋子里游荡着,仿佛这样游荡着,仿佛这样念经似的嘟囔着“不能丢”,那卡就会蹦出来似的。也许是累了,她一屁股坐在地上,怔怔地看着四周,目光像刚刚煮好的稀粥,是黏糊的。她想大哭一场,可是,竟然哭不出来,仿佛哭的神经被吓坏了,身体里的眼泪也被吓得蒸发了。她哭不出来。她哭不出来。她咧着嘴,像一只濒死的动物,瞪着两只眼睛,喉咙里发出干嚎的声音,刚开始,不是很强烈,逐渐,变得强烈起来,震颤着,由她的胸腔开始,遍布全身,然后从嘴里跑出来。她胸前的两块肉,也跟着干嚎的声音,颤颤地抖动,就像是两个挣扎的兔子。就连身体下面的那个器官也跟着发出干嚎的声音。尖锐的,撕裂的,疼,震颤着,电流般遍布全身。
金子的眼睛看到刚才吐在墙上的血。那滩血变成了一个狰狞的面孔,在嘲笑着她。一个面孔,两个面孔,在繁殖着,变成了太多面孔。它们是丑陋的,邪恶的,淫荡的,变态的……
最后,只剩下成光的面孔定格在那里。
“狗日的,找,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找出来。”
金子疯癫般从地上站起来,冲出门去。
二
凌晨的冷是那种可以钻进骨头里的冷,可是金子已经不觉得了,她的心里藏着火,藏着一团愤怒的火。一弯瘦瘦的月亮挂在天空的一角,像一把镰刀,锋芒毕露,摘下来就可以割麦子。还有,那些星星,闪着冷光,像藐视的眼睛。天空悄无声息,如同沙漠,如同一个巨大的岩层,冰冷坚硬地横在那里。
金子匆匆地走着,目光在街上寻找着出租车的影子。
清冷的大街上,只有一个清洁工,戴着口罩,挥舞着扫帚,在哗哗地扫着。
金子看见一个十字路口停了辆出租车,她飞奔过去,她轻飘飘的身影看上去像一片秋天的落叶。她透过车窗向车内看了看,那个司机躺在车里睡觉。她敲了敲车窗。司机懵懂地睁开眼睛,摇下窗户问了一句:“你要去哪?”金子说:“去向阳大街。”司机上下打量了一眼金子说:“十五块钱。”金子没有还价,要是在往常,金子一定会还价的,因为平时去向阳大街也就五块钱。可是,这个时候,金子身体里的火,烧得很猛,不能再等了,再等她可能就会被身体里的火烧成一把灰了,倒是省事了,省得进火葬场了。可,金子还不想,她还有垂垂病危的母亲,还有妹妹等在那里。金子拉开车门,坐了进去说:“快走吧。”司机没有动。“怎么啦?快走啊?”金子吼着。司机声音很沉着地说:“看你这一身,你不会没揣钱吧?一看你,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你别到时候下车不给钱啊?那我可就白跑了,现在汽油那么贵。”金子听了司机的话,火“腾”地涌上脑门说:“我干什么的,怎么了?我不会差你钱的。”金子说着,从兜里掏出一百块钱,说,“你看看,够不够。”司机看见金子手里的钱,笑了笑,一边发动车辆,一边说:“大妹子,不是我势利眼啊,是以前我真的碰到了你这样的人,下车不给钱,还跟我放骚……”金子火气十足地说:“我这样的人怎么了?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好人了吗?再有一点办法,谁干这个啊?还不都是生活逼迫的吗?我知道很多人瞧不起我们,但我告诉你,我也是人,甚至比很多人模狗样的人还是人。”司机连忙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一看你大妹子就是一个爽快人。”金子懒得听司机的话,连忙说:“别罗嗦了,快走吧。”这个时候的金子没有时间跟这样一个无聊的人磨叽了,她的心早已飞到了向阳大街的那个麻将馆了。她希望成光能在那里。这个时候的金子恨得成光牙根都痒痒的,要是成光在身边的话,要真的是成光偷了她那个卡的话,她能把成光用牙撕了,嚼吧嚼吧,连肉和骨头都吞了。
出租车停在向阳大街“蓝溪棋牌娱乐室”门口,金子接过找回来的零钱,就冲进了棋牌室。这家棋牌室是一个叫钉子的女人开的,她以前也干跟金子一样的活,后来跟一个派出所的人好上了,还给那个男人生了一个儿子,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开了这家棋牌室。一些姐妹们,无聊的时候常来打打麻将,她们开钉子的玩笑说,她算是找到了一个好的靠山了,没想到这枚钉子钉得还真准,一下子钉上了一个穿制服的,看来我们这些圈是没这个能耐了。大家说完就哈哈大笑。金子也是在这里玩麻将的时候,遇到的成光。
出租车司机头探出窗外,鄙视地看着,点了一支烟,在门口等活。
金子冲进蓝溪棋牌娱乐室的时候,屋里没有几座在玩麻将的。金子的目光像刀片一样,“刷刷”地掠过那些人的脸,找着成光。成光竟然不在。
这个时候,棋牌室的老板娘看见了金子,喊着:“金子,你来了,玩一会儿吗?”
金子气哼哼地说:“不玩,成光今天来了吗?”
钉子看金子的脸色很不好看,再看她的穿着就知道出事了,她连忙问:“金子,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
金子就是一个劲地问:“成光今天来了吗?”
钉子说:“来了,好像赢了五沓吧,跟老五他们玩去了。”
金子问:“你知道他们上哪玩去了吗?”
钉子说:“不知道。”
金子说:“他们就没说吗?”
钉子说:“没说。”
金子一下子就瘫软在一个椅子上了。
钉子问:“到底怎么了?”
金子说:“那个天杀的,偷了我的钱,偷了我的钱。”
钉子不吭声了,给金子拿过来一瓶饮料,放在金子的面前说:“他今天赢了,我想成光,不会是那种人吧,他只不过拿你的钱周转一下。”
金子瞪了钉子一眼说:“他妈的,等我找到他,看我不……我这急等着用钱呢?”
金子看着钉子的目光突然变得柔软了,她说:“钉子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我妈病了,妹妹打来电话,说要住院,要交很多钱。”
钉子一听到金子要借钱,脸色连忙变了。还有,金子说这些话,她听得太多了,甚至自己以前在客人的面前也这样装可怜过。她鄙夷地看着金子说:“我现在手头也不宽绰,今天早上,老张刚刚把钱拿走,放到股市里了。他这是拿走我们娘俩的命啊,你说,我还不能不给吗?”
金子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尤其是钉子这个人,她把钱看的比命还重要。以前她们在一起干的时候,有一个月钉子怎么干活都撵不上金子,钉子假惺惺地说请金子吃饭,结果,钉子在金子的酒杯里放了半片安眠药,金子睡了一夜,没干活,钉子的营业额就撵上来了。这件事,金子一直耿耿于怀,倒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钉子这个人。她后悔刚才跟钉子说借钱的事,她就是一个铁公鸡,一毛不拔。钱就是她身上的肉,给了别人或借了别人,那就是割她的肉。
金子说:“就当我没说过。”
金子警惕地看着桌上的那瓶饮料讪笑着说:“这不会给我下药了吧?”
钉子不好意思地说:“金子,你还记得那事呢?那时候年轻气盛,你别记恨姐啊?”
金子说:“没,我没。”
金子起身要走,钉子说:“金子,我真的没钱借你,你别生气啊?”
金子哼了一声说:“切,我生什么气呢?”
金子说完就走,钉子在后面送着。在金子要上出租车的时候钉子突然喊住金子说:“成光他们在海华娱乐玩呢,他不让我跟你说,我看你是真的有事,你见到他的时候,别说是我说的。”
钉子的话像风一样刮走了。
金子走出钉子的棋牌娱乐室,心里恨恨地暗骂:“狗日的成光,狗日。”金子觉得两腿很沉,像灌了铅似的。眼皮也很沉很沉,随时都准备把眼睛关进去。她打了一个哈欠,看见那辆出租车还没走,她拉开车门说,去海华娱乐。她倚在座位上,两只眼皮直打架,像两片小小的雨刷器。她心里的火熊熊地燃烧着,只觉得口腔发干,舌头发硬,发疼,像一小块木头。她狠狠地在自己的大腿上掐了一把,困意顿时驱散了不少。她看着司机说,大哥,有烟吗?我的忘记带出来了。司机掏出烟递给她,“啪”的一下,打开打火机,跳跃的火苗看上去像一把匕首。金子动作缓慢,她太疲惫了,把烟叼在嘴里,对着那把匕首伸过去,烟点着了,她狠狠地吸了一口,仿佛要把那股烟吸进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似的。她倚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说,大哥,我迷糊一会儿,到了,你喊我。说是这么说,可是金子哪能迷糊着啊。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都在成光那里呢。或者说,自己的命都在成光手里攥着呢,要是那些钱真的没了,她也不活了。她在心里暗骂着,男人都是狼,是狗,有着狼心狗肺的下水。
秋风呼呼地刮着,像有人在哭。路边的树木被风刮得东倒西歪的,几乎要连根拔起。金子瑟瑟地抱紧自己,不但没有感觉到温暖,反而感觉更冷了。因为她的身体是冰冷的,像一个死人。金子有过一回跟死人接触的机会。两年前,一个姐妹因为得了淋病,受不了病魔的纠缠,后来跳楼了,是金子去给她收的尸体。那天,金子抱着那个姐妹,为她化了妆。本来这些不用金子做的,可是金子做了。金子甚至还作了一件大家都想不到的事情,金子在花圈店给那个姐妹扎了一个帅哥,是那种看上去很老实、很善良的帅哥,烧给了那个姐妹。后来,还是有很多问题,从殡仪馆出来,金子捧着骨灰,竟然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个姐妹的一切联系方式都是假的。没办法,金子只好模仿电视里那样,把那个姐妹的骨灰撒在了这座城市的一条大河里。那次以后,金子发狠多多地挣钱,然后金盆洗手。没想到,老天爷捉弄她,出了这件事。金子的天塌了。钱对于金子来说就是她的天。金子的地陷了。钱对于金子来说就是她的地。在这一刻,金子多么希望有一个人能抱抱她,或者让她依靠一下。她看了眼司机,把目光又收了回来。她鄙视男人,一切男人。在这一刻,男人就是她的仇人。她的目光变成了一把刀片,“唰”地扎向司机的脸上,深深地刺,割着,刮着,仿佛要揭下那层脸皮,血淋淋的。金子佯笑着。她突然开玩笑地对司机说,大哥,你找过小姐吗?司机愣了愣说,没。金子不相信地说,怎么可能?司机说,没那个闲钱,再说了……
金子没有继续追问下去。她本来想对司机说,我就是小姐,你想吗?但她没有说。她竟然对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和想法,感到一丝羞耻,像吃了一只苍蝇。她感到自己怎么那么不要脸,那么掉价,那么不把自己当人,那么叫人恶心。她自己就是一只苍蝇。这样想着,她打开车窗,冷风吹在她的脸上,像一个巴掌,在扇着她的耳光。耳光响亮。想哭。眼泪就来了,顺着眼角流了出来。心伤了,肝伤了,肺也伤了,金子觉得浑身都疼,像蚂蚁在咬,在啃。司机看了金子一眼,想说什么,却没有说。金子感觉到司机在看她,连忙伸手抹掉脸上的眼泪。她恨铁不成钢地自责着,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哭什么?你就是一个婊子,一个×,有人会同情你吗?这个喧哗的城市谁认识你,他们只认你的肉。你是什么?你是肉。比猪肉贵不了多少的肉。她这样想着,坚强地挺了挺脊梁,像一棵荒岩上生长的麦子。眼神傲慢,鄙视地看着天光中的一切。它们僵硬,冰冷,没有一丝暖和气。这也许就是她眼中的城市。即使有暖和气,也让人感觉是虚假的。城里人太实际,对于她这样的人,她知道自己是什么?她在心里重复着,你就是肉。肉。比猪肉贵不了多少的肉。金子在控制自己,不要想了,现在是找到成光,找到那张卡,找到她的命,然后救她母亲的命。钱是一条链子,无形中连着很多人。钱是刽子手,随时都可能杀人,而且出手无影,无形,杀人不见血的那种。
尽管出租车开得很快,但金子的心就像一颗核弹头,穿过那些层峦叠嶂的建筑,飞进了海华娱乐。它在寻找着成光,寻找着那个让她心伤了,肝伤了,肺也伤了的男人。
三
出租车刚刚停稳,金子推开车门,甩给司机一张钱,就冲进了海华娱乐。大厅里有一个服务员在打盹,因为马上就要天亮了,没有客人了。老板也允许服务员打一个盹。也许是金子推开玻璃门的声音,惊醒了他。他睁开惺忪的睡眼问,女士,你干什么?金子吼着,我找人。服务员说,你找谁?金子没有回答,而是大声地喊起来,成光,你给我出来,成光,你个王八蛋,你给我滚出来。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厅内回荡着,像一个导弹,随时都可能爆炸。服务员被金子的喊叫声吓得清醒了。他说,女士,请你别这么大喊大叫的,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金子眼睛瞪着服务员说,狗屁了,我知道他在这里。狗日的成光,你给我出来。服务员想制止金子的喊叫,可是金子急眼了说,如果你想让我给派出所打一个电话的话,那你就给我把成光叫出来。服务员藐视地看了眼金子说,随便,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的老板是谁。金子的恐吓没起任何的作用。她冲上楼,在走廊里,仍大声地喊着:“成光,成光,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有些休息的客人,被金子吵醒了,从门缝里伸出头来看着,冒出一句“神经病”,又关上了门。服务员警告着金子说,如果你再喊的话,我就叫保安了。我想,你也不想太难堪了吧?金子理都不理那个服务员,一把推开他,目光射在他的脸上说,你给我滚开,姑奶奶也不是省油的灯。金子从二楼跑到三楼,从三楼跑到四楼,一路喊着,叫嚣着,根本不见成光的影子。金子开始怀疑钉子的消息是否准确,说不定金子骗了她。狗日的钉子,她诅咒着。服务员再次上前阻止金子的喊叫,金子猛地吐了一口唾沫在服务员的脸上说,你滚。服务员生气了,一边擦着脸上的唾沫,一边上来拽着金子。金子火了,伸出手给了服务员一个响亮的嘴巴。服务员手捂着嘴巴,怔怔地看着发疯的金子。金子已经拐上了五楼。金子的嗓子都喊嘶哑了,喊出来的声音细长得像一条灰色的,湿淋淋的带子。金子声嘶力竭地喊着,成光,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给我滚出来。
这时候,一个光头从一个房间出来,看了看金子说,你喊什么?金子看着光头说,我找成光。光头说,成光不在这。金子来到光头的身边说,钉子说成光在这。光头说,什么钉子,锤子的。这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你识相的话,快点离开。金子再怎么说,这些年见过的人多了,她根本没把光头放在眼里。她推开光头,闯进了那个房间。只见房间里云山雾罩的,呛得人直咳嗽。几个人坐在桌边打牌。他们看见金子闯进来,都回头看着。金子喊着,成光呢?他死了吗?一个中年人说,成光不在。金子的眼睛在牌桌上看着,她一下子就看到了那个打火机,那是金子前不久给成光买的。他一把抓过打火机,没管那套,上来就把牌桌给揭了,嘴里叫嚣着,成光,你给我滚出来,你要是不出来的话,我把这个房间给点了,你信不信。金子打开打火机,就要往窗帘上点。光头过来一把抱住了金子。金子挣扎着说,你别抱我,我知道成光在这,他要是不出来,我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不信,你们就看看。那个中年人看了眼金子说,还从来没看见过你这样的。金子瞪了那个中年男人一眼说,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赶快把成光给我叫出来。中年男人看了看其他几位,嘴里喃喃着,疯了,简直疯了。金子见成光还不出来,她的火“噌噌”地窜上脑门,两个太阳穴疼得几乎要爆炸了。中年男人说,成光刚才是在这的,可是,他刚接了一个电话,走了。金子说,不可能,我打他电话,他关机了。中年男人说,我没有必要骗你,电话是打到吧台的。金子的眼睛在中年男人的脸上扫描着,她在权衡着中年男人话的真假。中年男人还说,昨天一晚上就成光赢了,赢了五万,我看你还是回家等着吧,等着成光给你一个惊喜吧。金子不屑地看了一眼中年男人说,我不稀罕他的钱,我只要我的钱,他把我的钱给我就行。金子半信半疑地四处看着。金子还是不能相信。房间里紧张得气都喘不过来。就好像身边有无数颗雷,稍不留神,就是“轰”的一声巨响。那几个男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金子,有一个胖男人的目光在金子的胸脯上瞟着说,妹子,你在哪旮旯坐台,我有时间去揭你的台。金子没搭理那个男人,翕动着鼻子,四处闻着。要是成光在的话,她能闻出成光的味。她就像一条嗅觉灵敏的警犬,四处嗅着。成光真的不在。现在怎么办?金子不知道了。她的心里,茫茫然,而空荡荡的。整个人都抓瞎了。她恨死成光这个人了。还好,这时候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叫梁光明,四十多岁,嘴里喜欢叼着一个烟斗。他是海华娱乐的老板,金子以前在“大东方”做的时候,就认识这个男人,但那时候还不是海华娱乐的老板。这是一个出手很阔绰的男人。可能是那个服务员看金子不是省油的灯,就给梁光明打电话了。梁光明叼着烟斗走进来,看见是金子,他就笑了笑。梁光明说,这不是金子吗?金子抬眼看着,脸猛地一红,一热,火辣辣的。这种被人认出来的感觉就像被突然扒光了衣服,赤裸裸地出现在人的目光之中。这一红,一热之后,金子看了看梁光明,回忆着,突然想起来了,金子嗲声嗲气地喊着,这不是梁老板吗?你怎么出现在这里了?你也来赌博的吗?你看见成光了吗?金子的语速变得快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成光的下落。梁光明的眼睛很毒,一眼就看出金子遭难了,也看出自己认出金子,让金子有些尴尬。他是一个很会办事的人,任何人都不会得罪,包括像金子这样的人,再说了,金子对他也是一个有恩于他梁光明的人。梁光明看了看四周的人说,都散了吧,改天我做东,请大家好好地戳一顿。梁光明的话像雷声,还没等他的话说完,那个光头马上就行动了,开始收拾东西,把牌桌扶起来。其他的人也说,既然梁老板说话了,既然梁烟斗说话了,我们就撤吧,改天再战,就是便宜了成光这个臭小子。梁光明冲着金子说,你跟我到我的办公室吧。金子扭着身子跟在梁光明的身后,她本想上前挽着梁光明的胳膊,但没敢。梁光明狠狠地吸了一口烟斗,喷出的烟雾在他的头顶缥缈着。
房间里刚才瞟着金子胸部的胖男人说,这个女人到底是哪的?长得还真不错,很有女人味,改天打听打听。另一个男人说,这是成光的马子,你就算了吧。胖男人说,我看不像,我看成光到像是这个女人养的小白脸。他的眼睛透过门缝看见走廊里,金子扭动的屁股,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说,看来梁烟斗认识这个女人,还有,大清早的,那梁烟斗一定不会让这个女人闲着了。胖男人笑着,满脸的肉褶。他的目光已经把金子嫖了一回。
从金子认出梁光明的那一眼,她就把梁光明当成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知道这根稻草会不会救她的命。从以前的那件事情上看,梁光明还是一个有情有意的男人。金子看着梁光明的背影,没话找话地说,能有两年不见了吧?梁老板干大了,这海华娱乐竟是你开的啊?你看你越来越发福了。梁光明没有回答。走廊里的灯光照在金子的脸上。金子的脸看上去是那么的没有一丝血色,煞白煞白的,像一张白纸。两片嘴唇也白得像两条死蚕。金子跟着梁光明走进了梁光明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悲壮。
梁光明对金子说,把门关上。
四
金子从银行出来,也已经是中午了。日光毒辣辣的,让金子感到一阵的眩晕。她晃了晃虚弱的身体,扶着银行的玻璃门,休息了一会儿。她掏出手机给妹妹打电话,可是两个手机都没电了。她嘴里骂骂咧咧的,恨不得把手机摔了。她的情绪坏到了极点,她想杀人。想杀了那个狗日的成光。从银行出来,她找到路边的一个公共电话,给妹妹打了电话,语调低沉地对妹妹说,钱打过去,两个小时以后应该能到,你好好照顾咱妈,姐还有点事,办完了就回去,这城市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姐回去就不会来了。金子说得自己想哭,眼眶里就滚出两颗粘稠的叫做眼泪的混蛋东西。二嫚在电话里说,姐,你怎么了?你哭了吗?金子说,姐没哭,没。咱妈怎样?二嫚说,看上去好点了,今天早上还喝了一碗稀粥。金子说,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咱妈,姐就你们两个亲人了,还有,你也要好好学习,姐这样累死累活地挣钱干什么,不就是希望你有出息吗?过人上人的日子。二嫚说,姐,我知道,你也要注意身体,地里的麦子要割了,你早点回来。金子说,姐知道了,姐挂了。金子挂了电话,擦了下眼角的泪水,看着熙熙攘攘的马路,噪音四起。尖锐的噪音狠狠地扎着金子的心。茫然的虚空,虚空的心都没底了。成光这个大骗子在哪?金子想。金子的肚子里饿了,咕噜噜地响起来。金子穿过马路,找了一家小店,要了一碗豆腐脑,慢慢地喝着。她吃什么都没口味。软软的,嫩嫩的豆腐脑进入口腔,让她一阵的恶心。那碗里的豆腐脑在她的眼睛里竟然是红色的,红红的。金子撂下了,不吃了。她站起来,猛地又坐下了。她头晕得厉害。
金子坐在小店里望着那碗让她恶心的豆腐脑。一只巨大的绿豆蝇飞舞着落在了碗沿上。金子下意识地轰了轰。那绿豆蝇嗡嗡地飞着,金子伸出手去抓,一下子就抓住了,捏了一手难闻的汁液。金子喊着,服务员,来几张餐巾纸。出来的服务员是一个大肚子的孕妇,她腆着肚子出现在金子的面前。金子抓过餐巾纸擦着手上苍蝇的汁液,抬眼看了一下服务员的肚子,高高的隆起着,像一个气球。金子的眼睛往上撩了一下服务员的脸,她眼睛一亮,嘴里喊出,阿花,阿花。那个服务员目光躲避着金子的目光说,你认错人了,我不叫阿花。金子还说,我是金子,你不认识我了吗?服务员脸色难看地说,我不认识什么金子银子的。她说完就扭身走了,走到了后厨。金子质疑地看着,嘴里喃喃着,难道是我真的认错了吗?她不是阿花吗?不是吗?过了很长时间,金子才缓过神来。阿花是不想让人认出她来。不想让人知道她的过去。金子的心沉沉的,像坠了一块石头。她站起来,只觉得脚背上湿漉漉的,她低下头,丝袜和鞋上被一种液体浸染着,她惊惧地心里跳了一下,又跳了一下,她的身体里缓缓流着血。她不知所措地偷偷地看着四周的人,没有人留意她。她纳闷地喃喃着,怎么提前就来了呢?她有些尴尬地快速走出小店。她甚至还回头看了看小店,小店的名字叫:“幸福小吃部。”她在心里默默地祝福阿花。那血从她的身体里缓缓地流淌出来,大街上的人已经发现了,惊惶地看着她。她狼狈地拦着车,想回去,可是出租车看她那样子,都怕弄脏了车座,拒绝拉她。金子谩骂着,两腿发软,身体轻飘飘的,像踩在棉花上。
马路上有一个被汽车压碎的瓶子,碎玻璃折射着日光,像一只只眼睛。
金子蹲在路边,突然嚎啕地哭起来。眼泪昆虫般地飞出来。这不像她的性格,但她哭了。她的哭声对于她个人来说很大,甚至可以说巨大,但很快就被四周喧嚣的声音淹没了。
五
金子的心这时是伤透了,整个身体仿佛都漏气了,可以听见吹进去的风声。也许是仇恨的力量,也许是那没有找到的金钱的力量,金子勉强地站起来,两手扶着酸痛的腰。一阵眼冒金星。那些小星星闪闪烁烁着,让她眼前的事物变得摇晃起来。摇晃。金子记得有一次从租碟店租了一盘碟,是那个长头发的店主向她推荐的。没想到回去一看,是一个国外的,还带着唱歌,动画什么的,金子不是很喜欢,但金子在吃东西的空间瞄了几眼,有一个画面还是令金子震撼了。那个画面说的一群人站着排,顺着传送带落进一个绞肉机里,然后变成了肉馅。很残酷。很暴力。但金子记住了。今天,金子再一次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就想起了这件事情。她硬撑着身体,走了几步,又站住了。她在停下来的时候恢复着体力。眼泪把她的身体的水分哭没了。经血把她的身体的血流空了。她空空荡荡的,像一个行走的木乃伊。她这样想着。她眼中的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地下墓场。她看见那些男人暧昧的笑脸,丑陋、狰狞。她从那些面孔中辨认着成光的面孔,她看见了,看见了。当她喊叫着的时候,一切化为虚无。她微微闭上眼,让自己回到现实中来。她迷失,她找寻,她的方向在时间存在的可能之中,也可能不在。在时间的墙壁上,她的涂抹呈现的也许是一种荒诞。但她存在了,她涂抹了。在挣扎中,她成为人。
火辣辣的太阳晒得这片地方直打颤,既冷酷无情,又令人疲惫不堪。也许是因为体力不支的原因,金子倚靠在路边的一个电线杆上歇息着。她的眼睛看着前方围了很多的人,还有警察。她心里对警察有些惧怕,但现在,她不怕了,她没有交易行为。她沉重的身体在慢慢地下坠着,直到坐在地上。日光很暖和,毛茸茸的,落在她苍白的脸上。那群人还有警车围着一栋大楼,警灯闪烁,人声嘈杂。过了很长时间,金子看见那栋大楼在一声巨响中坍塌了,烟尘四起。金子的身体也随之一颤,怔怔地看着,才缓过神来,才明白,原来那是在爆破一栋大楼。随着大楼的坍塌,人群渐渐地散去。金子孤单地倚靠在电线杆上,竟然感觉到来自电线杆的温暖。这种温暖跟体温不一样。一个骑着三轮车的的老头,从她的身边经过,金子喊着,三轮车,三轮车。老头看见了她问,干什么?姑娘。一句久违了的姑娘,让金子心里温暖了很多。以前她爹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叫她,姑娘,俺们家大姑娘。金子对老头说,大爷,你拉活吗?老头问,拉什么?金子说,我。老头疑惑地看着金子。金子说,我病了,想让你拉我回家。金子跟了一句,我给你钱。老头看了看金子苍白的脸说,那就上来吧,姑娘。金子缓慢地移动着,坐到了三轮车上。三轮车板很硬,咯得金子屁股的肉很疼。血还多多少少地从金子的身体里流出来。老头看见了,有些惊骇,老头明白了。他的眉头蹙了几下,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却没有说。金子看着老头,真的有些像她爹,她眼睛一热。她没话找话地问,大爷,这么大岁数了,还干啊?怎么不在家养老啊?老头表情痛苦地说,挣口饭吃,工厂倒闭了,发出不出退休金,不干怎么整,总不能坐在家里等死吧。金子不问了。老头说的是什么?就是活着,活着本身就是沉重。
一只小蚂蚁爬到了金子的膝盖上。金子看了看,轻轻地拿开了。
三轮车快到小区的时候,金子说,停吧,大爷,我到了,多少钱?老头看了看金子说,姑娘,本来我不打算收你钱的,可是,你女人的那血流到了我的车上,你也知道,老话说,那血是晦气的,我拉完你,就不能拉别人了,我要去洗洗我的车,你就给个洗车的钱吧,两块。金子没觉得老人的话有什么,掏出五块钱,给了老头说,不用找了,谢谢,您,大爷。老头很倔强地说,一定要找你的。老头掏出他的一个小包,从里面拿出三个硬币递给金子。金子没去接,硬币掉在了地上,滚动着。金子看见老头佝偻着腰捡着硬币,有一个硬币跑到了路边的草丛里,老人几乎是爬着过去捡的。金子鼻子一酸,走了。等老头找全三个硬币,喊着,你的钱,你的钱。金子已经走进了小区,不见了。
六
金子慢慢地,一步一晃地,手扶着楼梯,向楼上挪着。楼道里是黑的。黑色在吞噬着她的身体。她的身体成为黑暗的一部分。她是这么感觉的。没有找到成光的她,是绝望的。心碎的。怨恨的。气愤的。如果,现在成光站在她的面前,她一定会使尽全身的力气给成光一个嘴巴,打歪他的脸,打掉他的牙,甚至要扑上去,用嘴咬他的肉,喝他的血。她咬着牙,一步步地挪着沉重的身体。她这样想着,又开始咒骂自己,你一个贱X,你见过的男人还少吗?你怎么就相信这个男人呢?你傻瓜啊?你的脑袋看来是被门框给挤了,你简直一个傻×,你……这个世界,什么是可靠的呢?自己。人是免不了做牲口的。人,就是牲口。男牲口和女牲口。
一阵难言的酸楚从她的心里滚过,像硫酸的液体,正在腐蚀着她。她浑身没有一丝力气,她停下来,手抓着楼梯喘息着。气息微弱。静静的楼道内,阴森恐怖。她仍能听见心脏微小的搏动。她喃喃着,也许我要死了,但我不想就这么死在城里,我要死在那个麦浪滚滚的乡下,还有麦田边那细细的溪流边。她开始恐惧死,她呜呜地哭了。她咬了咬牙,坚持着,上楼,来到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她就摔倒在地板上。过了很长时间,她才挣扎着,从地上爬到床上。一、两米的距离,她爬了很长时间。那一片狼藉的地面,还有那些藏着她梦想的书。现在,一切都不重要了。她躺在床上,眼睛看着窗外的星星。眼泪“唰”地流了出来,成了一个泪人,被含盐的泪水腌制着。时间是黑色的,屋子是黑色的。只有窗外的星星亮着,像一只只嘲笑的眼睛,散发着冷光。那是城市的星星,长在城市的天空上。傲慢、霸道地鄙视着躺在床上的金子。金子伸过一只手,拉上窗帘,把城市挡在了窗户外面。空荡荡的屋子,有几分的冷清,像一个巨大的冰窖。她又神经质地拉开窗帘,目光像导弹在瞄准着天上的那些星星。那一刻,她觉得天上的星星都被她击落了,熄灭了。星星掉下来的地方,出现一个个洞,像一个个空洞的眼窝。她冷笑了一声,她笑什么?因为她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一个叫女娲的女人。
过了一会儿,金子勉强地爬起来,去洗了澡。
温热的水流中,金子再一次哭泣。她心中的绝望像一只手在抓挠着她的内脏。她萎顿地坐在了浴缸里,任由那水淹没自己。她沉潜着,沉潜着,不愿浮上来。水中的世界是温暖的,像母亲的肚子,像胎儿时期羊水的世界,是安全的。水中的世界像一个通道,让她看见了金色的麦田,看见那金色的日光在麦芒上闪烁,昂扬的麦穗,像上生长着,尖尖的麦芒指向天空。一群飞鸟从麦田上空飞过。天是那么的蓝,蓝得清澈,蓝得深邃,因为蓝而变得旷远。
金子猛地从水中窜起,甩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缸里走出来。她浑身变得轻松起来,赤裸的脚轻盈地在地面上走着。她看见镜子里细嫩白皙的身体,是那么干净。她喜欢地看着自己的身体,下意识地摸了摸。她的眉头皱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是的,就是这个身体晃动在午夜的华都洗浴中心,在那些男人中间周旋着,像一株移植的麦子,从来没有真正生根发芽过。就是成光这个让她有一丝信赖的男人,现在也不可靠了。也是一个王八蛋。她抓着浴巾疯狂地擦拭着,似乎要擦去某种身体上存在的痕迹。她擦了几下,又回到浴缸中,浸泡在水中,直到水在慢慢地变凉,她才走出来。她冷静了很多,擦完后,扯过挂在墙上浴袍,没想到,成光的那件浴袍也挂在那里,和她的浴袍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她扯下成光的浴袍扔在地上,拉过自己的穿在身上,回到房间。她找出手机,插在电源插座上充电。一闪一闪的红灯,像一只红色的眼睛。
金子点了支烟,狠狠地吸着,“哧哧”燃烧的烟,像愤怒。
鬼金,辽宁本溪人。1974年出生。有小说在《十月》、《作家》、《花城》、《上海文学》、《山花》、《青年文学》等杂志发表,有诗歌在各期刊发表。有小说入选《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出版小说集《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长在天上的树》《秉烛夜》等。小说《金色的麦子》获第九届《上海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