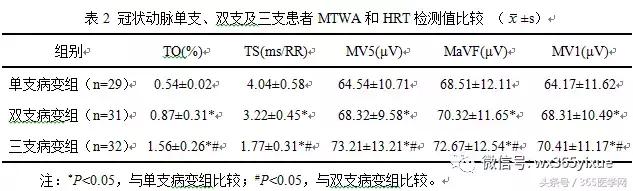“香格里拉有三十多家藏家乐,这家算是比较文雅的,有些真的是夸张。”扎西顿珠面无表情,这个壮大的康巴汉子专心从掌心里捏炒青稞吃。
舞台上是藏家比武招亲的戏码,一位最终胜出的光头胖子脸上被草草地画上张飞式的眉毛和格萨尔式的胡须,额头画上爱心,胡乱地背上叉子枪,插上藏刀、挂上护身符盒子“嘎乌”,上百名游客在下方大笑欢呼,并在各自导游的调动下比赛欢呼和跺脚的声音。
“雅索,雅索,雅雅索!雅索,雅索,雅雅索!”新藏居的木地板随之索索地落下灰尘。
胖子游客手足无措地站在场中间,沉重的叉子枪背在身后,对于刚下大巴,被缺氧的想象所折磨的游客,藏家乐敞开怀抱,满足了他们九成对于藏区的想象。
招亲节目又是经过各家“藏家乐”或“土司家宴”的实践证明最有效的方法。那些经历了长途旅行,肿胀疲惫的面孔终于随着跺脚、狂呼而变得快乐起来。
背景音乐是香格里拉弦子。
中甸人在弦子的伴奏下载歌载舞 本文图除署名外均为 杨江涛 图
属于商队的城市与它的音乐
“我从文化感情上不喜欢藏家乐的表演,太夸张,为迎合外地游客的口味改变了弦子的很多动作。藏家乐的演出抹杀了弦子的特色。”扎西顿珠这位香格里拉弦子歌词的翻译家和收集者说,但他也无法评价藏家乐是否应当存在下去,三十多家藏家乐,每天要接待数千游客。
兹事体大。关系到香格里拉的转型。
这座曾经的独克宗古城、后来的中甸,如今的香格里拉,每年要接待近1500万名游客,是本地居民数量的一百倍。团队游客出入精品酒店、大理银企、台湾陶笛和华丽夸张的藏刀店铺。小资们则蜗居于小院子里,歌颂松赞酒店,乡下农庄的自治奶酪,野生蜂蜜,或者宣称自己去寺庙里时,堪布(方丈)特意用经卷在她脑袋上敲击了两下,而别人只有一下。
香格里拉的地位以前并不如此。1940年代,当时的中甸县,后来的香格里拉还是“一座怪凄凉冷落的边城衙门”,“清凉得像一座尼姑庵,只有四五天一班的邮差,才会带来一些一个月以前的报纸来”。90年代初期,中甸的高大夯土墙面上还用石灰书写着毛主席语录和文革标语,在高原地方,标语保存得格外长和鲜明。镇子的中心道路是砌着大石块的商道,被驴马蹄铁磕碰得斑斑点点,镇子上甚至开着好几家出售马蹄铁、马鞍和马铃的小店。
那时候,香格里拉是一座属于商队的城市,横跨亚洲,联系汉藏的一条商道从这里通过,它的使命主要是为商队服务。
从汉地来的商队进入香格里拉后,前方就横亘着令人生畏的横断山区。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构成漫长的、支离破碎的山系,水路运输完全无法通行,马脚子驱赶着马、骡、驴,从一条狭窄的干热河谷上升,越过海拔超过4000米的山口,进入另一条更加艰险的铁锈红色河谷。
20世纪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感慨道:“要走到这个地区是一件很艰难的事儿,因为它是亚洲最孤立的地区。新疆肯定是遥远的地方,但汽车和飞机使它接近文明。而这里也许从来听不到汽车的喇叭声,因为要在这样的高山深谷地区修建一条公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一条道路后来被称为茶马古道而人尽皆知,但其意义并不至于茶和马这么简单。
香格里拉,或者说跨越横断山脉的康巴地区,几乎所有来自远方的物质和文明种子都来自这条东西走向的道路,只有最贵重,最有利可图的物资能够负担得起这一跨越驼峰的昂贵贸易路线,例如茶叶和丝绸。
这一东西走向的贵重物资长途贸易对于西藏和汉地的意义,已经被无数次地强调,马队将至关重要的文明孢子吹入天险阻隔的横断山腹地,使得这一区域的文明展现出迷人的万花筒色:康巴马夫们肩背英国步枪,带领驮运汉地丝绸和瓷器的马队,渡过湍急河谷,两侧密宗寺院和天主教堂隔河相望。
云南香格里拉 资料 图
然而,如果认为横断山区只能东西向展开,那就是错误的。
澜沧江和金沙江从北向南而来,带来充沛的水汽,沿着河流起伏的道路,其艰险不下于茶马古道,同样是横断山区文明传播和物质交换的重要孔道,这一南北通道,在茶马古道的宏大视野下,却往往被忽视。
以黑陶为代表的手工艺、康巴式建筑技术的传播、盐和粮食等大宗物资流动,军事征服,族群迁移和宗教的扩展,这些更为重大和缓慢的浪潮,主要沿着南北向的河谷传播,甚至天主教传教士在高原扩展,也是沿着金沙江、澜沧江两条流域由南向北渗透。行政区划上,这里分成西藏、云南、四川、青海四个省份,但就流域而言,其实同属一个康巴文化圈。
同样是沿着浑黄的金沙江、澜沧江的河谷而传播的,是弦子。虽然可能起源于遥远的北方草原,但如今弦子已经成为横断山康巴地区的代表乐声。甚至被拉萨人称为“康谐”,即康巴之歌。
东西向的艰难远程商道,南北向同样艰险的本地交流,使得被大山与河谷分割的康巴地区拥有了一种奇特的弹性。地理决定了这里令人绝望的孤立,但是脆弱破碎的山间商道依然维持着有限的往来,人类的财富和精神,以行脚和马蹄的缓慢速度深入大山的肌理,维持着脉搏。
这是一种有趣的状态,开放得极为有限,却又不过于孤立,两者互为左右,一静一动,如同两根震荡的弦,冲击反弹,反复拨动康巴的琴弦,甚至造就了康巴人特有的矛盾性格。
如果你认准了康巴人是固守河谷的农人,你就会突然发现他烈火一样大胆商人和亡命马脚子的性格;如果你认定他是大胆的商人,他的保守和顽固又让你吃惊,他会把全部的力气都播种到土地里。
这是康巴人命定的二律背反性格。
无怪弦子的旋律并没有交响乐一样事先考虑周全,精妙严整的结构,而是一顿一挫,敞开而又关闭,无尽地回旋往复,随时可以任由天然,临时创作,最后又总是落入到同一个旋律上来。
弦子是汉语的意译,在香格里拉当地被称为“仪”。弦子的起源从来就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商人之歌,有的说是农民之歌,也有的说是流浪艺人所带来。扎西顿珠认为,弦子来自北方草原,进入横断山区之后,不再继续向东翻越大山,而是沿着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南下传播。最早的琴筒是野牦牛角所制,进入河谷地后,变成木料所制。
在漫长的河谷传播中,香格里拉弦子是其中较南的一支,在金沙江、澜沧江流域,弦子从南向北,在香格里拉、芒康、巴塘直至玉树都有分布。甚至在澜沧江的下游,缅甸等地也有近似弦子的音乐。
我们无法以现代音乐的概念去理解弦子,它更近似于孔子所谓“礼崩乐坏”中的乐,而不是西方式的音乐,弦子首先是仪式而不是音乐,它是载体更过于本体。
拉响弦子的乐器——毕旺
弦子的乐器演奏、歌唱和舞蹈是不可分的,共同构成节庆或者仪式。至少在传统观念中,并没有将艺术从仪式中抽象出的概念。因此,一听到弦子乐器“毕旺”(或说弦胡)的乐声,机智诙谐的歌词就会在舌尖上滚动,男人的膝盖会摇摆发热,女人的袖子会凛凛生风。
“弦胡曲扎加措,配件所需多多,琴柱杜鹃树枝,琴筒柳木树干,羊皮来做鼓面,雄马马尾作弦,金色码子作鞍,银色旋柄一对。拉起动人琴弦,内心无比欢喜。”这是弦子词里毕旺的制作手法。
如今琴弦多用尼龙弦代替马尾弦,琴弓如今使用马尾,原先用牦牛尾。演奏者手持毕旺,将琴身置于大腿上、怀中,缓慢跳舞,你可以想象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将小提琴竖立在胸前,边拉边跳舞的场景。但弦子的腔调比小提琴浑厚,更近似于康巴汉子们悠长的歌声。
香格里拉的康巴汉子们会选择用毕旺而不是藏刀作为自己的象征,礼乐比射御更重要,孔夫子对此或许会大加赞赏。所谓“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大概也是如此:男子先拉弦起舞,女子随后与之对舞,彼此应和,一首歌只能用一个曲调。曲调的套式花样繁多,词却可以自由发挥,甚至临时篡改,曲调一变,舞步也要跟着改变。跳弦子如同对垒,一边要舞步洒脱,节奏自然,同时还要拼命去想现编什么词。
歌词即生活
思无邪,于是词像白云一样圆滚滚地涌起在红土山脉的尽头。
——“前方的路途像一条巨大的哈达,我是一个卷着哈达而来的少年。天边的云朵白如海螺,我将去往更多吉祥幸福的地方……”
一套完整的弦子舞,包括开始曲、迎宾、相会、情歌内容、赞颂、离别、挽留等段落组成,当大家唱完了全部曲调,歌词也再编不出后,就会加快节奏起舞,直到最后所有人都气喘吁吁,才算结束。
在清代与民国时期,弦子遍布整个康巴地区。据清《绥靖屯志》记载:“新春之时,多有歌舞之举,即跳歌装与跳弦子两种也。…其舞蹈之人不拘其数,或集数户,或仅一家,或男女相分相合。杂陈酒肴,围桌而跳,歌声婉转,长袖飘扬,一殇一歌,洵有别致也。”
《西康纪要》记载“跳弦子之事,西康巴安乍丫等处极为盛行,且有以此为职业而浪走江湖者,故西康各处均有之。”
香格里拉地区流传的说法是,佛的世界最早形成,然后是法的世界,然后是歌舞的世界。扎西顿珠觉得其含义是,佛,法和歌舞有内在的联系,高深奥妙的智慧可以通过最简单的方式来传播,例如弦子。
在乐曲、舞步、歌词三者中,最灵活也变化最快的是歌词。
原本弦子的歌词就可以即兴发挥,康巴的民间诗人们捻着胡须,顺手就把词给编出来,无论是赞美,挽留,或者是讽刺,都信手拈来,满满地浸透了山地的智慧,也夹杂着商路带来的讯息。
即兴的词,又是最脆弱,最容易流失的。它是香格里拉人生活的忠实样本。其中大量的弦子歌词是关于经商,瓷器、茶叶、枪支、地图纷纷出现。
“汉地中心所产的,八宝图纹瓷碗,斟满可口的美酒,怎能叫人不馋……”
“骑花马的叔叔,请把花马借给我。不会远走高又飞,到巴塘理塘就归来。”
“花马不会空返回,我驼来藏茶十三驮。驼来十三驮茶叶,到拉萨寺院打个茶……”
前往拉萨的商路,一去可能数月,如果从缅甸或者西藏江孜前往印度,没有一年时间无法回转,河谷居民们也唱歌离别。
“夏天莫说要走,鲜花会感悲伤;马鹿莫说要走,草坝会感寂寞……”
“江头江尾水,分别时间已太长,同在庙堂里,净水碗中能相聚……”
有些歌词甚至绘出了这个地区的地理样貌,贯穿商路的全过程,西到拉萨,东到康定。
“拉萨建在哪里,拉萨建在大海上,昌都建在哪里,昌都建在两河间,察雅建在哪里,察雅建在岩石上,巴塘建在哪里,巴塘建在大鹏上……”
这商路的口头地图,竟然在整个弦子河谷引发了私下的竞争,似乎通过弦子歌词的改变,能够把握这条商路的主导权,把握想象中的河谷弦子世界的话语权。
例如在香格里拉,商路上的重要地点除了必不可少的拉萨和昌都之外,四川的巴塘、理塘、康定则被德钦、中甸、大理、丽江所取代。香格里拉人唱着这首弦子,或许会感觉那条漫长的古道变得更加亲切可见。
川藏北线的各县城,同样将自己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放了进去。
在争夺谁才是真正的香格里拉、香巴拉、川藏南线、北线以及滇藏谁才是茶马古道主干道的背景下,这首弦子就显得更加有趣了,似乎道路和山脉自己会写歌、唱歌。
扎西顿珠说,他有点想不明白,当年基督教传进来之后,依然坚持把自己的赞美诗、唱诗班的那一套带进来,根本没有想过用弦子这种方式传教,否则传播得会肯定会更远一些。那时,我们或许会听到歌颂横断山圣母玛利亚的弦子歌词。
仪式中,男子先拉起弦子起舞,女子随之与其对舞
除了商业,更重要,也更隽永的歌词是情歌。
情歌并不热辣,并不大胆,似乎不符合人们对热烈的康巴式爱情的想象,更多是试探,如同《诗经》中的情歌,一是出于礼节,二是小心试探,一方面,少女们不可能立即对途经此地的马脚子立刻敞开心扉,另一方面,如果不加以暗示,或许他明天就会上路。
这是一场爱情冒险,通过弦子歌词的试探,牵引砰砰乱跳的心脏,呼唤少年们一次次走上爱情与财富的道路。
“姑娘好像银做的摇铃,众人都说有裂纹。有无裂纹己放在你手中,请你细听一下铃声……”
“杜鹃与雨水之间,虽无相会的约定,当春季暖风吹佛之时,必然相聚是命中注定……”
商队的马脚子们路过村庄,和村民跳弦子对歌,看对眼就留下的很不少。马脚子如同翅膀短小的蜜蜂,虽然飞得不远,却满满地携带着弦子的花粉,带着文化的密码和爱情的气味,一个村庄接力一个村庄,使得孤立的河谷不再贫瘠。
有些弦子歌词传播之远,生命力之强,甚至进入了神圣的宗教殿堂。那位著名的诗人仓央嘉措本出生在喜马拉雅山以南,可他绝妙的道歌和弦子情歌极为契合,都是每句六字,四句一组,甚至分享巧妙清新的比喻,他写道:
“初三月儿光光,银辉清澈明亮,请对我发个誓约,要像满月一样……”
弦子的消失与传承
但弦子所包含的众多密码,还是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有些歌词逐渐没人穿唱,最终消失。更为普遍的是,歌词的作者、所隐含的意思、触发的契机已经无人知晓,甚至弦子歌名的含义都变得无法理解。
“索多亚拉”,或者“阿吉拉冲”,是一首副歌的名字,或者是一句隔着山谷的呼喊是甚至暗语?阿克向巴,次仁错姆,是马脚子在路上遇见的某个传奇男子,或者是最终分开的情人吗,是否应当意译成慈悲大叔,长寿海中仙女?骑着花马的大叔,是不是跳舞时如同踩着弹簧一样轻盈?扎尼尼玛基参是那位弦子王的名字吗,或者不过是一位漫游者?
这些歌名代表着横断山区的千百次邂逅,空落下的泪水,是一张张生动的山区地图,是空余名字的一千零一夜。它们的曲调还在流传,交换,但最初产生的契机,则如同扯碎的松石串珠滚落沟壑,就这么消失掉了,真的是找不回来。
歌词也会带有鲜明的时代标记,旅游开放和信息时代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不仅歌词中出现了发电机,水电站,计划生育,甚至最顽固的唱法和舞蹈都发生了改变。
原本三四月间不跳弦子,老人说那是播种的季节,“所有的种子都已经入土,而种子也有灵魂,也有喜怒哀乐,种子入土之后,如果唱一些伤感的弦子,种子就不愿意出土。”
还有情歌,只能对着同龄人甚至陌生人,在亲人、父母、兄长面前是唱不得的,这是最令人尴尬的行为。如今,三、四月份的香格里拉,接待游人的弦子一直在唱,情歌演唱随手就来,毫无避开亲人的必要。年轻的弦子歌手纷纷推出自己的专辑,原本不可分离的歌与舞因此独立存在,个人随意地填写歌词,加上电子配乐。
节庆上身穿传统服饰的藏区少女
于是传承成为了一个问题,
“传承!听上去是一件伟大的玩意,但如果仅是一种缺乏思考和策略的口号,那就未免让人生厌了。没有创新,就无从传承!变化业已发生,很多东西丧失了赖以存在的载体,就像没了天空的鸟儿,就像失去海洋的鱼群。我们能否创造和提供对等的条件或环境、形式等重新赋予那些东西以生命,这才是关键!德国著名学者赫尔曼·鲍辛格在其著作《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一书里,认为传统文化的没落与价值变异无关,而肇始于技术革命以及与其相随而至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在下对此论断深以为然。”
这段话来自次陈,他是一名香格里拉的作家,同样热爱弦子。
“以前交通非常闭塞,两个村子的人确实一两年才能见面欢聚,所以唱:‘我们多时未能相见,就像金鸟飞散在山坡上;我们近日如愿相聚,就像金鸟同栖一颗树子上’,那时很贴切实际的。现在很多人整年在一起,还唱这个词的时候,就感觉很空洞。”他解释道。
“就弦子而言,本地文化人都会哀伤地指出,人们没有像从前那样热爱它了,它必将沦为一种标本式的存在。但细想,在通讯技术和交往方式单一的年代,弦子其实是有一些实际功用的,特别是在年轻群体中,表情达意、互诉爱慕都是通过弦子完成的。如今人们可以有更多选择结识新人,弦子真正的魅力在这种技术革命中暗淡下去。”
“所以,我对于“把弦子原封不动地传承下来”这种想法一直挺悲观的,可行性越来越小,也不觉得必须这样。这种偏执间接地把弦子文化逼进死胡同。必须超越很久以来“照搬式”的对民间弦子的整理方式,在完全消化民间素材的基础上,有力体现自己的创造力,以赋予弦子文化新的可能与希望。”
虽说看得分明,但次陈自己所爱的也是更传统的弦子歌曲。
关于弦子的矛盾将继续下去,这并不特别让人为难,在康巴之地众多的矛盾与反复震荡中,不过又增加了一个矛盾。
对我来说,重金属摇滚以及弦子,各自表达着这片红土山地的不同侧面。商队经行的山地以多声部在发出轰然巨响。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这片暗红色山地,走在干燥的山间小道上,四下无人,突然听到了顿挫、曲折的拉弦之声。
这音乐曲折盘旋,让你脚踩飞尘,登上山巅呼吸,想要身无分文漫游世界;但同时又让你想要裹挟着痛苦,落回温暖闭塞的河谷大地,回到家乡。
那么,这就肯定是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