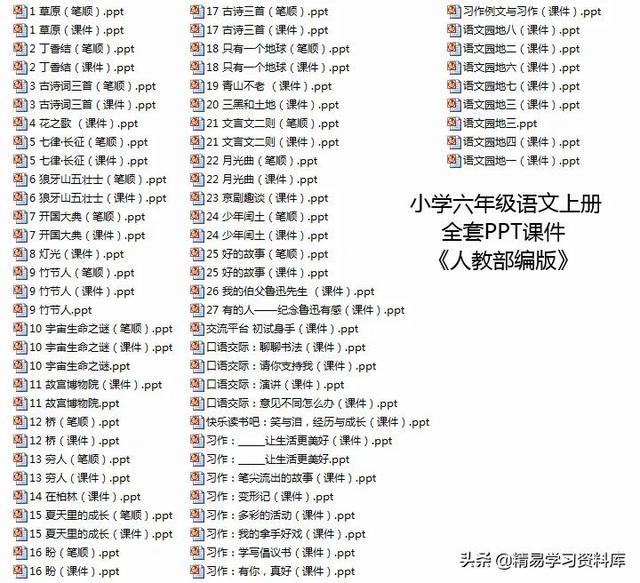自上次文章中稍微点到小满同学后,小马同学有点醋意:为什么不给我推送一篇!
其实,我早有执笔为其写点东西的想法,奈何鄙人一直患有重度拖延症,加上先前时间也不允许,也因我是个感性的人,需要酝酿充沛的感情,所以终究拖着没写。恰好,还好,近来时间尚有盈余,情绪亦因某人某些事低沉下行。
鉴于此,执笔挥墨,以文字下酒,思念远方的他。
谈到此文,首先得从标题《我远方的兄弟——小马同学》说起。小马同学要求如下两个标题:《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追风少(骚)年,如今却在远方的远方》、《那个比女朋友还贴心的北方兄弟,我欠你一句再见》。
我说,这TM也太长太矫情了,标题放不下你的娇柔与做作!
他说,你自己想办法,lao 子对你就是这样的,要真实一点!
哦,他还要求放一首赵雷的《理想》。所以现在还可回到文章开头,点一下播放键,边听边看,边看边听。
但,标题终究没遂他的意,奈我何,哈哈哈哈哈哈。因为我觉得以上两个标题会让世人觉得我很矫情很做作,虽然小可感情细腻且充沛,但向来是“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不是流于表面之人,我所写所书,皆是言之有物,必是情之凿凿。
毕竟,我深谙小学语文试卷中心思想的答题秘诀: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以乐写哀情更哀。这就是所谓的“蝉鸣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一位哲人也曾和我说过,哭出来的是泪,笑出来的是血,大致也是这个道理吧(所以,有了“杜鹃啼血”这个传说)。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一起来揭开小马脸上的神秘面纱,有请12位佳丽亮灯。
小马来自北方,准确地来说,应该是来自西北方,正是“西北玄天一片云,凤凰落进乌鸦群”的西北方。我也记不清他是在祁连山下,还是阴山脚下,抑或是天山脚下,这并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非官方渠道信息,据传在他头上,不对,是他在山下有一片绿油油的广袤的一望无垠的大草原(春天来了,亚欧大陆东岸的太平洋又准时准点地刮来了一股如期而至的湿湿的厚厚的水汽,它们越过秦岭淮河一线,穿过在什么山上凿开的一个大洞,牵着一匹小毛驴,偏偏就不骑,来到了他的这片绿油油的大草原,而草原上的动物们也到了交配的季节···咳咳,不好意思,进错频道了)。
民间传闻:他的草原上放养着1000只羊,2000头牦牛,3000只兔子,所以他姓马!小的时候,他总是骑着头羊(恰似《指环王》里的矮人国王一样),手持钢鞭,放养着999只羊、2000头牦牛、3000只兔子(因为他骑着头羊,所以只剩999只),像指挥着千军万马一样冲锋陷阵、攻城略地,封燕然山,勒石记功,所以他叫“马军”。
第一次见小马同学,他就泪眼汪汪,轻易让人相信,上辈子他欠我的,恰似宝玉初见黛玉时“这个妹妹我曾见过”。不,我们的初次见面绝不是这样的!!!初见,并未有浪漫与温情,也不曾有过“微风和煦,夕阳的余晖打在他的侧脸上”这么唯美,因为他的侧脸好像还有青春痘,哈哈哈哈。
我们的第一次相见,是在去年7月的一个周末,小满同学邀我们一起打球,话说我现在也还不知当初他们是怎么相识的,总之我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结识了。那天太阳落得很晚(因为是7月啊,哈哈哈),他装备齐全地站在小满同学的宿舍外,倚着走廊半高的墙,深情地单手托腮望着远方,宛如一个玛德智障。
说到第一印象,他当时染着黄毛烫着发,小小的眼睛,单眼皮,面带恶相,显得有点痞气,不过有点当年我读书时的风范,哈哈哈(请看我当年的年少轻狂)。
我已记不清小满同学是否有介绍我们认识,因为当时他在宿舍内拖拖拉拉换着衣服,也想不起我和小马同学是否有过尴尬的寒暄,反正大部分时间我们两个就这样站在宿舍外,假装在玩手机,等着另一个玛德智障小满同学,偶尔催催那个换衣服的玛德智障。
第一次和小马同学打球,我觉得他还可以,虽然技术糙了点,投射能力差了点,但还好他有身高,有体重,可以在内线打打、挤挤,虽然脚步不行,像我学不会恋爱一样,他总学不会背身左转上篮,但还是可以在球场上辅佐我的。
对了,第一次打球,小马同学给我和小满同学付了门票钱,中场休息的时候,他还走了很远的路去给我们买了水。虽然,打完球我们就把钱转给他了(微信也是那个时候加的,因为要转钱,哈哈哈),但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可交,值得托付终身。后来熟了,就是谁走在前面谁掏钱,哈哈哈哈哈,当然偶有通过投篮比赛的输赢决定谁掏钱。
此后的日子,我们仨每周一必在单位球场打球,周六选择性打球。当时,我们号称“魔鬼三叉戟”,令对手闻风丧胆,脱裤就跑。因为我们的配置极其合理,做到了资源的完全优化配置,联系实际,充分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个人主观能动性。小马同学打内线,小满同学不要命的扛着球往里冲,而我则掌控全场,适时地在外投篮杀死比赛。
篮球,必定会伴随着伤病。作为三人年纪中最大的老大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有一次我就不幸扭伤脚踝,痛苦倒地,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并伴有痛苦的呻吟声(此处,应有哀伤的音乐),就像烤肉一样需要不停地翻炒,还有孜然粉吱吱吱的声音。事后,小马同学说,我呻吟得太yin dang,太ji ba尴尬了,哈哈哈哈。
那晚,小马同学搀扶着我上地铁下地铁,上楼梯下楼梯,像极了那年朱自清父亲的脚步蹒跚,深一脚浅一脚地去买橘子,只是至今我不知道,买橘子的是我还是小马同学。那年那晚,我们还没有车,如今的我——依然打不起车,哈哈哈哈哈哈。
回去的路上,小马同学给我买了冰水,一直敷着;回到住处,小马同学给把他的跌打损伤药全给我拿来了,叫我好好喷涂好好休养。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也把脚摔瘸了,那晚也是我们搀扶着他回来,给他带晚餐给他带药,药就是上次他还没用完的。哈哈哈哈,是兄弟,就一起摔瘸腿!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什么容易,除了长胖和秃头。第二天,班还是得照样上,是小王同学搀着我一起去的(后续有机会也得写写小王同学,他也是一个神一样的男人),因为小王同学去得早,小马同学起得晚。
午餐时间,一个摔断腿的我,何去何从,不知午餐在哪里。就在我迷茫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小马,是的,是他,是他,就是他,我们的小马同学。他已经帮我叫好外卖,叫我别乱动,去会议室等着。过一会他就拿着外卖进来陪我一起吃了,还帮我丢了餐盒(泪水不争气地就流了下来,我感动得泪眼婆娑,潸然泪下,无法自已)。
花前月下,池旁垂柳,有酒必有我,有我必有酒。
我和小马同学的故事,酒是必然少不了的,毕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我和小马同学第一次喝酒,也是和小满同学一起的,也是去年的7月底。那时我们参加集团集训,海边露营,小满同学给我打了个神秘电话,叫我偷偷地到海边的小船上,虽不知详情,我依旧欣然赴约。
原来小马同学偷偷带了3罐酒,还有一袋花生米,几袋小鱼干等下酒菜。那晚,我们沐浴着月色,听着海浪声,喝着小酒,放着赵雷的《理想》、《三十岁的女人》等民谣。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亦无法饮酒,听不到杯子碰在一起,亦听不到梦想破碎的声音。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集训庆功宴尾声,我走在盘旋着的楼梯上准备摆驾回宫,不知从哪里冒出好多醉醺醺的叫不出名字的小伙伴要拉着我喝酒,我一一应承下来,准备返回继续喝,毕竟我是那颗最耀眼的星。
也不知道小马同学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硬把我推上了大巴,说:喝个球!并叮嘱小王同学,不准我下车。在去门外大巴的路上,厕所里有趴在地上吐的,酒店大堂里有躺在地上不愿起来撒泼的,门外石阶上有晕晕乎乎不说话的,120救护车来了一辆又一辆,和打的一样。
那晚小马同学的及时护驾,完美地阻止了我继续饮酒,也中止了我后半夜的下半场。我还是很感激的,毕竟小饮怡情,大饮伤身。次日大家酒醒,都在那里嗔怪我,说那晚狂野的气氛与基调就是我给搞起来的。哈哈哈哈,确实,那晚一开始我就直接让全场的酒局进入了高潮,一直不停。
就在不久前,走在下班的小路上,我收到小马同学的语音:卧槽,我发现我每次喊你,不是去喝酒,就是在去喝酒的路上,哈哈哈哈哈。但随后,就是两人的沉默的黯然神伤。
后来的每个周末,我们都会邀上小满同学、小王同学等一起饮酒吹水,或烧烤或火锅等等等等,还记得在大排档时,我点了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也许是送给自己,也许是送给在场的每一个人,毕竟谁还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男孩呢,因为一说如果,心就疼了。总之,斑驳的记忆里,纸笺开始慢慢泛黄。
我特别喜欢在支着顶棚的大排档吃饭,喜欢听穿梭在各个餐桌前拉着音响的小姐姐唱歌,因为我觉得那样好有烟火气。那时的我们没有钱,但很快乐;现在的我们依然没有钱,但我们好像不再快乐。后来,酒桌上的人再也凑不齐了,就剩下了我和小马同学。
两个人喝酒,总少点气氛,我们俩也很少去外面喝酒了,就经常到小卖部里买几瓶酒,一点下酒菜,在宿舍里抑或是在顶楼的楼梯口,慢慢地饮,缓缓地聊,喝完就回去睡觉了。那时,我们特喜欢喝珠江零度,觉得特别甜。
小马同学总是和我吹嘘,说他能一直喝。我不知道他酒量到底多少,亦如他也不知道我酒量多少,但他总是认为他酒量比我大。我唯一一次见他吐是年会那晚,车子刚到小区门口,他就火速滚下车,扶着门口那颗老槐树狂吐。当然,我肯定也是先拍照,再照顾他,亦如前不久我生日那晚,在前面10几米处的那颗老槐树下狂吐的情形一模一样。
小马同学也是个有生活情调的人,虽然宿舍环境简陋,但他总是趁着周末给我做饭。每次我尝完第一口,他总是沾沾自喜一脸神气地问:我做得好吃吧。其实,他从不知道我打小就开始自己做饭,一个人做饭一个人吃。冬至那天,我们在宿舍打火锅的情形至今历历在目,只是锅不在了,人也不在一起了。
小马同学总认为他做饭比我好吃,酒量比我好,球比我打得好,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认为他比我帅。他不知道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比我帅的没我聪明,比我聪明的没我帅。只是至今也无法得知他到底是没我聪明还是没我帅。(他唯一官方承认不如我的是文学水平没我高,这一点我也是认同的)
小马同学还是个挺会照顾人的人。去年的冬天,我重感冒发烧,畏寒怕冷,全身瘫软无力,他知道后,立马把身上的呢绒大衣给我穿,小王同学那天也脱了自己的风衣,给我披上。下班回到宿舍,我直接就躺床上了,但被子真的好薄,他又给我拿来了一件很厚很厚的衣服帮我捂在了被子上,还帮我把被子等掖好按紧。
后来,我走了,去了一个叫“深渊”的地方,那里有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还有几个很坏的老巫婆(他人赐名)。那段深渊里的日子,虽然短暂,痛苦却格外漫长,水深及膝,淹腹,一寸一寸漫至喉咙,浮在水面的两只眼睛也被完全淹盖,还在按着我的头往下淹。
那段时间,小马同学要么在地铁口买好了宵夜啤酒等我,要么周末大老远地跑过来陪我加班,他不敢发出任何声响不敢说话不敢做任何动作,因为那段时间我特压抑特焦虑,随便一点声响我就会大声斥责他,他就躺在床上默默地玩手机,等着我去吃饭。偶尔还帮我打扫卫生,收拾房间。
再后来,他要走了,他要回他的那片大草原了。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是周五,暴风雨,飞机航班都延误了,大家决定为小马同学践行,他们一大早就告诉我,下班后一定要来,我答应了,我说我一定争取过来,只是可能会晚点。
可是,就像那天的航班因暴风雨延误一样,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叫我别回去了,叫我留下来去机场接一个毫无关系的来自北方的陌生人,叫我留下来加班,准备周末两天的活动。然后,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就去吃饭了。
看着微信群里发来的视频:这杯敬小马,这杯敬伟哥。我说:我今晚可能来不了了···然后,放下手机,哭得和傻逼一样,痛苦流涕,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哭得难以自已(敲打这段文字的时候,眼睛还是湿润了,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淌)。因为我知道,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小马同学了,我却无法在临别的酒桌上,和他喝着酒,说着临别的话(所以,小马同学拟定的标题里说:我欠他一句再见)。
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吃完饭就回来了,他找我要烟抽。我赶紧擦干眼泪,给完烟立马就闪出了他的办公室。然后他就走了,临走前还交代买点水果、宵夜好好招待那个从北方来的陌生人。然而,那个要回西北方的男生,我却无法给予我最后的践行。(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叫我给他带午餐、晚餐,买宵夜买水果,给他那群“朋友”买宵夜买水果,从未给过钱,甚至连谢谢都没有一句)
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走后没多久,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时,那个很坏的巫婆又打电话过来,说她文件没弄好,叫我帮她做一下,明后两天急着用,现在下暴雨她就不回来了。
那个暴风雨的夜晚,我终究还是没能去为小马同学践行,甚至连释放情绪的时间与机会都没有(那晚,我饿着肚子没吃饭,因为本打算和小马同学一同吃饭一起喝酒)。我一直工作到次日4点多,6点钟就得起床招待那个北方来的陌生人,然后又开始了周末两天的白加黑的连续加班。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从未有过感激之情,隔天还是那副很坏很坏的尊荣,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也就是这次事件,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座“深渊”,离开那个很坏很坏的秃头的地中海男人,离开那些很坏的巫婆,他们残忍无情麻木地剥夺了我的快乐、我的笑语、我的尊严,也剥夺了我为小马同学最后的践行与告别,剥夺了我说“再见”的机会。(可悲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却总是让你坚持,他们却从不问你经历了什么承受过什么,也不会去考虑继续坚持对你意味着什么)
小马同学就这样走了。走之前,他把他那串在西北方某寺院开过光的菩提子手链分成了3份,一份送给了我,一份送给了小满同学,而那串手链我至今还带着。
小马同学就这样走了。再也没人陪我深夜饮酒,再也没人陪我加班,再也没人帮我打扫卫生,再也没人给我做饭,再也没人陪我逛街,再也没人拿着宵夜在地铁口等我,再也没人帮我冒雨搬家,再也没人在我生病受伤时照顾我,再也没人····
小马同学就这样走了。
后来,小马同学和我说,他在草原上过得很好。开着车,喝着酒,唱着歌,一切都很好。
我想,往后的岁月,也许很难再见,但彼此岁月静好,就是最完美的落款了吧。
我的思念没有落款。小马同学,再见!
胡说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