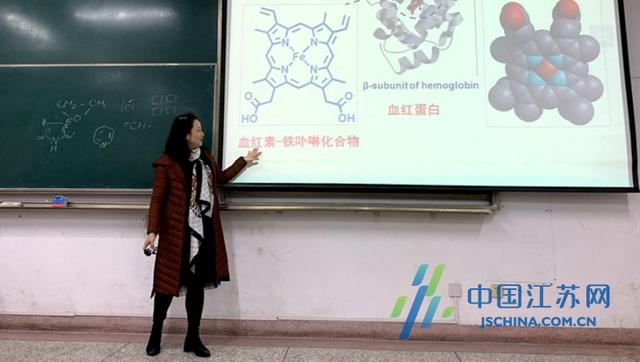我的马列主义 艺术(art)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一般的美学理论,他们也没有对艺术和文学进行过任何系统的研究。马克思对这个问题顺便说的话与其说提供了一个可确信的解释原则,不如说更多地引起了争论。在《大纲》(导言)里的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话中,马克思提到:“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不是同物质基础的发展成正比例的”。他接着指出:就希腊艺术来说,虽然它跟社会发展的特殊形式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一定的方面它对我们仍然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并具有“永久的魅力”。这种看法也就表明,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些类型的艺术不是严格地由社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它们具有永久的、超历史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提示了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在别的地方,马克思嘲笑那些“被莱辛讽刺的18世纪的法国幻想主义。既然我们在力学等方面大大超过古代,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造史诗呢?”上述的观点可以使艺术“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而且,这些观点也跟恩格斯在19世纪90年代里写的几封信中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比较广泛的论述相一致。
另一方面,在有关艺术家的社会地位问题上,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的“唯一者”的概念时指出:“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特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单纯的画家,只有把绘画作为自己多种活动中的一项活动的人们”。在这里,如果根据马克思关于消灭劳动分工重要性的总的观点,艺术本身作为一种特殊活动的存在都成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这一思想不仅纯属推测,迹近“替未来的餐厅泡制食谱”,而且从其字义上看,它对于任何复杂和技术发展的社会都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于艺术创造来说。但是,它表明了一个特别是贯穿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概念。从这种概念出发,无论是艺术还是一种发展的美学意识,都象语言一样被看作是一种人类所普遍特有的能力;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虽然只有一部分人在社会中担负知识分子的工作,但是,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艺术家。
具有开拓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著作是由梅林(在1893年)和普列汉诺夫(在1912年)写作的。梅林所主要关心的是文学,而不是观赏的艺术或音乐。普列汉诺夫则旨在发展一种严格的决定论,他说:“在我看来,任何人民的艺术总是跟他们的经济有着密切的因果联系”。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他分析在原始社会中,舞蹈是表达劳动的愉快(如狩猎),而音乐则是对劳动的协助(通过节奏)。但是,他在阐述劳动、游戏和艺术的一般关系时指出:尽管艺术的产生具有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功利的源泉,然而审美的乐趣则具有自身欢乐的理由。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除了原始社会,经济只是通过阶级区别和阶级统治所起的中介影响作用来间接地决定艺术。例如,他在谈到18世纪法国戏剧和绘画时指出,它们表现了“优雅的贵族风味”的胜利。但是,在该世纪后期,随着贵族统治受到资产阶级的挑战,布歇和格勒兹的艺术则“在大卫及其学派的革命绘画面前相形失色”。
苏联的十月革命和在中欧发生的革命运动,把两个在某些方面相对立的主题——革命艺术和无产阶级艺术——引向争论的前沿。在苏联,在1917—1929年期间任教育和艺术人民委员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少制止对先锋派的引进”;例如,他支持由夏达尔任校长的维切布斯克艺术学校,还支持由坎金斯基、偑夫兹纳等人执教、并成为“构成主义”摇篮的莫斯科艺术室的重建。在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也支持艺术中的先锋派,尽管这个运动在政治上失败,它的一些成就(如格罗皮厄斯的建筑之家)在法西斯胜利前一直幸存。本世纪20年代初期,在苏联和德国的革命艺术的代表人物之间还存在一种活跃的交流关系。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艺术(或文化)的观念,受到一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他们中有托洛茨基)的批判,并且达到了把无产阶级文化组织看作是党的敌手和潜在反革命组织的地步。但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认为无产阶级需要有它自己的阶级艺术、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是有“党性的”这样一种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强制下成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美学教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制度下,是谈不到在艺术中进行激进的试验或先锋派运动了,于是一种沉闷平庸之风便盛行起来。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完全排除艺术上的新颖思想,利夫希茨(他曾经与卢卡奇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共事)除了编辑第一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艺术的评论集之外(该书在1937年出版),还在大量地参阅马克思的笔记和早期著作的基础上,发表了一部很有意思的有关马克思美学思想的论著。
可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及后来,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在西方做出的。布莱希特提出他自己的“史诗剧”来跟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相对抗,他是这样地评价卢卡奇及其在莫斯科的同事的:“直率地说,他们是创造的敌人,他们自己不要创造,(而是)扮演着衙役的角色并实行对他人的控制”。布莱希特的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本杰明的美学理论,他把史诗剧看作是如何能使艺术创作的形式和手段朝着一种社会主义方向来加以改造的模式。布莱希特跟卢卡奇之间的论战,其实是一场内容更为广泛的论战的一部分,那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即以新的内容充实起来的19世纪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和“现代派”(特别是德国的表现主义,以及立体艺术派和超现实主义)的支持者之间的一场论战;“现代派”的支持者除了布莱希特和本杰明以外,还有布洛赫和阿多尔诺。
拉斐尔的那部包含三篇关于艺术社会学的论文的著作,是本世纪30年代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另一个主要贡献,但只是在近年才广泛地被人们所知道。在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的论文中,作者从对马克思《大纲》(导言)的原文进行详细分析着手,去建立一种艺术社会学,以便克服辩证唯物论“至多能在个别艺术问题上进行一些不确定的、零碎的研究”的现存弱点。拉斐尔强调马克思关于希腊神话是经济基础与希腊艺术的中介这一观念的重要性,并提出一系列的神话和艺术的一般关系的新问题。他还考察了有关物质生产和艺术的“不平衡发展”的各种问题,最后他批判了马克思关于希腊艺术的“永恒魅力”的解释,以为这是“跟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对于希腊艺术其所以在欧洲历史若干时期中具有艺术的“标准价值”,拉斐尔自己的解释则是:每当经济和社会变革使得整个文化经历危机时,就会出现“复古”现象。在这些论文中的第三篇中,拉斐尔认为毕加索的艺术是现代派最为典型的例子,并指出现代派是跟自由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有关。
在过去20年中,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艺术的著作明显地以方法论的论著为主(即抽象地制定一种合适的马克思主义的艺术概念),只有为数不多的论著从事一些实质性的研究。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克林詹德尔就工业革命中的艺术这一专题所作的卓越研究,在这里,他特别注意了艺术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新型的人”的力量的增长对艺术的影响作用;他的这项研究完成比较早,但最近又重新发表。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威列特对魏玛时期的德国在绘画、建筑和音乐方面的现代派运动所作的详细考察。至于最近的理论探讨,则集中在以下两个主题上:(1)艺术就是意识形态,(2)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基本表现。这两个主题从一开始就引起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注意,其根源则在于马克思自己对艺术的不同看法。
一方面,认为艺术就是意识形态而进行的分析势必要去说明,在一个统治阶级存在的特殊的历史阶段中艺术风格(包括形式和内容)在该阶级的整个思想观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这就必须像戈尔德曼在文学创作方面所主张的那样:首先要建立起艺术创作和风格的内在含义的结构,然后再确定结构在一定生产方式的阶级关系这种更为广泛的结构中所占的地位。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拉斐尔,在上面提到的研究工作中,都曾试图这样做。另一方面,由于有一些艺术可以被看作是被压迫阶级争取其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于是,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便围绕着“革命艺术”的固有特性及其分析。近来,把艺术视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有意义的方面,是对通俗艺术和“文化工业”的兴趣的不断增长,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成员(如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著作,在这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根据他们的观点,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时代中的艺术,不仅由于机械再生产及其广泛传播而引进退化,而且还在促使互相争议的阶级和集团的安定联合方面具有较大的力量;同时,由于激进的创新容易被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机体所吸收,任何革命艺术的意识形态影响就被削弱了。然而,本杰明则持有相反的看法;在他看来,机械再生产的主要作用是毁灭了精英人物的艺术“光环”,是对“传统的摧枯拉朽”,并缔造了无产阶级与新的文化形式(例如电影)之间的联系。
人们把艺术主题看作是创造力的表现,从而提出了在分析美学价值和人性方面的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不仅直到近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相对上说仍不很发展,而且在过去20年来逐渐增加的一批著作还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的深刻分歧。不过,从社会实践的意义上说,把艺术看作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创造力的表现和一种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最终可以用理论术语来归纳),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马克思主义对待艺术态度具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艺术(像一般精神生活一样)应当自由地发展,形成“百花齐放”,而不是一定要去适应某种艺术教条的要求,特别是一种政治权力强加的教条;第二个原则是跟上面提到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思想大体上相符,也就是在容许优秀天才人物的“阳春白雪”发展的同时,要更广泛地把美术的创造活动作为一般人的需要和乐趣之源加以培养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