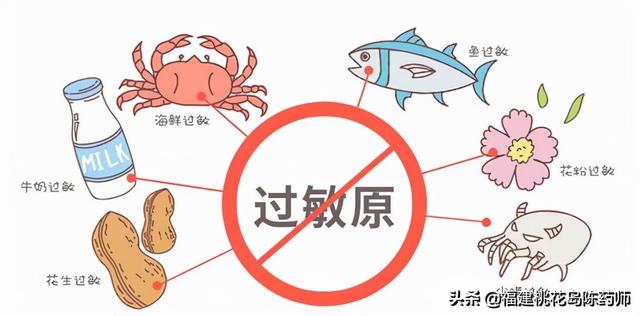卡夫卡在《变形记》中创造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在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与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但是这其中有一个人物对格里高尔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父亲。
不管格里高尔有没有变成甲虫,父亲似乎始终都是厌恶,看不起格里高利的。
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父亲吗?
对儿子冰冷暴力,好像仇人一般,一点温情都没有,卡夫卡心中的父亲形象又是怎样的?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这样描述他的父亲:
“您坐在您的靠背椅里主宰着世界,您的看法正确,别人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是偏执狂,是神经不正常。您是那样自以为是,以致您可以不讲理,总是您常有理。”
《致父亲》是卡夫卡在36岁时写的一封书信,内容就是控诉自己的父亲。
但是他本人并不敢亲自交给父亲看,就让母亲转交,可惜母亲最后也没有把信给父亲。
没错,在卡夫卡的家里,他的父亲海尔曼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以至于卡夫卡人到中年,都无法释怀,写了信给父亲却不敢给父亲看。
卡夫卡的父亲海尔曼出生于贫寒的犹太家庭,他白手起家,强壮粗暴,几十年经商后终于挣下一份家业。
从一无所有到富有财富,让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海尔曼变得刚愎自用,唯我独尊,尤其表现在家庭关系里,任何人都不能忤逆他的意志。
而作为海尔曼长子的卡夫卡身体瘦弱,性格怯懦,与海尔曼高大强壮的体魄,果断优越的性格大相径庭。
越是这样,海尔曼就越严格要求卡夫卡,但是海尔曼的教育方式是诋毁,是压制,往往通过打骂、恐吓、嘲讽等方式来督促卡夫卡按照他的意志来行事。
敏感怯懦的卡夫卡对文学产生独特的兴趣,那好像是他栖息的安宁之地。
但是父亲海尔曼坚决反对卡夫卡的文学追求,让其学习法律,好进入上流社会,出人头地。
无论是人生选择,还是生活兴趣,父亲都是专横粗暴得干预,这给卡夫卡带来非常严重的心理创伤。
但他本人并不敢反抗父亲的这种权威,只能将心绪都寄托在文学作品中。
暴力压迫者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的父亲就代表着家庭中的暴力分子。
而这种暴力,只针对家庭成员。
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无法准点起床赶火车,公司的经理赶来看看情况,却被吓得落荒而逃。
父亲首先做的并不是追回经理解释,而是抄起沙发上的手杖,想要先制裁格里高尔。
要知道,格里高尔的这位父亲已经五年没有工作了,甚至全家都没有工作,全靠格里高尔早出晚归地养活,还有父亲的债款,一直都靠格里高尔在还。
若是格里高尔丢掉工作,那么这个家的经济生活将岌岌可危。
父亲首先要做的,不应该是先帮助格里高尔稳定工作问题吗?
毕竟突发情况下,出事人也应该先解决外部矛盾。
但是偏偏父亲要站在儿子的对立面,先怪罪格里高尔。
父亲代表着家里的权威,即使是变成甲虫,格里高尔依旧心生惧意,后退着想要回到房间。
但是由于甲虫的身材过于庞大,格里高尔卡在了房门口。
尽管格里高尔已经在拼命地想往房间里爬,但是高大的父亲对儿子一点耐心都没有,直接朝格里高尔猛踹一脚,任由格里高尔受伤,然后“砰”地一声把格里高尔关了起来。
这种暴力行为在小说中不仅出现一次,甚至是格里高尔的致死伤也是由父亲的暴力引起的。
在全家都认识到格里高尔真的变成不能创造价值的甲虫后,便要搬空格里高尔房间里的东西。
格里高尔也明白自己如今的形象只会给人带来恐惧和烦恼,所以往往躲在角落里,不让家人看见害怕。
可是空空荡荡的房间,是刺骨的孤独。
那墙上的仕女画,是格里高尔唯一想保留的东西,所以他顾不上思考其他,就拖着甲虫的身体爬向墙上的仕女画。
胆小怯懦的母亲开门看见了这一幕,吓得晕倒过去。
回家的父亲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在格里高尔身上,怒气冲冲地要教训格里高尔,毫无疑问,父亲教训的唯一手段便是暴力。
餐盘上的苹果一个接一个地砸向格里高尔,一个苹果正中格里高尔的背部。
是妹妹的哭泣让父亲网开一面,放过已经瘫倒在地的格里高尔。
重新被赶入昏暗房间里受重伤的格里高尔无人问津。
两次冲突中,父亲都扮演着压迫者的形象,没有给格里高尔一丝的怜惜。
而格里高尔自己呢?
他永远选择的是忍受和退让,没有一次正面反抗,是不敢吗?
父权其实,在格里高尔家里,笼罩着严重的父权思想。
当然不仅是格里高尔自己,就连母亲和妹妹,都是在这种父权下生活。
五年前,父亲的公司破产倒闭,顺带欠下大笔债务,格里高尔任劳任怨,不辞辛劳地干着推销员的工作,不辞辛劳地养活这个家,不辞辛劳地帮父亲还债。
在格里高尔完全进化成甲虫后,靠格里高尔养活的一家人不得不自食其力,父亲也开始出门打工,找了一份银行杂役的工作。
但是父亲很喜欢在沙发上打瞌睡,就是要早起上班也不愿上床好好休息,一定要赖在沙发上。
《变形记》中这样描述:
“不管母亲和妹妹怎么好言相劝,他总要慢慢摇上十五分钟的头,闭着双眼,就是不站起来。母亲扯他衣袖,在他耳边说些好话,妹妹也放下功课过来帮忙。
可是这对父亲都毫无作用,他在沙发里坐得更牢了。”
即使是善意的劝告,父亲也听不进去,他习惯固执己见,习惯凭自己意志行事。
就像上帝,父亲这个角色成了家庭里唯一的决策人。
懦弱柔顺的母亲不会反抗,听话懂事的妹妹不会反抗,格里高尔也无法反抗。
这样扭曲的家庭关系,注定让格里高尔无法适应社会的生存。
他在家庭中,处于被压迫的角色,那在社会上,也容易处于被压迫的角色。
在小说中,格里高尔任职的公司就是一家吸血公司。
格里高尔不敢犯一点小错,甚至不能有一点疏忽,不然就会招致老板的怀疑。
五年里,格里高尔没请过一次病假,但一次因变成甲虫旷工,就被经理明里暗里地诋毁,甚至想要辞退。
这其实也照应了格里高尔的父亲的表现,与卡夫卡自身经历如出一辙。
望子成龙的父亲不能接受儿子一点瑕疵,儿子也拼命想得到父亲的承认和认可,可偏偏父亲的希望和儿子的希望存在着相反方向的矛盾。
两代人不仅在身体素养,而且在文化上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追求和表现。
父亲的种种暴行表现,让儿子既畏惧,又憎恶,并且无法斩断这种情感联系。
卡夫卡在《致父亲》中提起他孩童时期曾经由父亲带着去游戏。
父亲是高大强壮的,儿子却是瘦小羸弱的。
卡夫卡这样写道他当时对父亲复杂的感情:
“在更衣室里,我觉得自己十分寒酸,不仅是在您面前,在整个世界面前,我都自惭形秽,因为您是我衡量一切事物的准则。”
这里透露出卡夫卡对父亲深深的自卑和敬畏之情。
这是天生的,儿子对父亲有着与生具来的崇拜,但是儿子自身的不完美让其自卑,同时渴求父亲的认可。
然而父亲却从没有给儿子任何的赞许,随之而来的失望也是沉重的。
并且父亲影响着家里的每一个人,所有家庭成员给格里高尔带来的冷漠,都是从父亲那里发源继承的。
解脱当格里高尔是个“有用的人”时,冷漠可能不会发酵。
但是一旦格里高尔失去了价值,其他家庭成员就会完全服从于父亲的意志。
在小说中,妹妹对格里高尔的态度变化是最大的。
冷漠的家庭里,格里高尔无法把感情寄托在父亲身上,也无法把感情寄托在父亲的忠实顺从者母亲身上,就只能把爱倾注在妹妹身上。
妹妹开始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不用为钱担忧,不用为衣食发愁,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妹妹喜欢拉小提琴,格里高尔就想着攒钱送妹妹去音乐学院。
格里高尔可以说是竭尽所能地对妹妹好,妹妹呢,对格里高尔也是有真感情的,在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前期,只有妹妹愿意进格里高尔的房间,给格里高尔送吃的。
可是最后格里高尔受到美妙的小提琴声音吸引,情不自禁地爬出房门,吓跑了房客,破坏了妹妹的小提琴演奏。
妹妹便崩溃了,她嚎啕大哭,让父亲赶走格里高尔。
对妹妹的感情是格里高尔对这个家庭唯一的希望,这个希望破灭后,格里高尔平静地接受死亡。
“他静静地思考到凌晨三点钟,隐约自窗口处望见一丝晨曦,随即无意识地垂首,通过鼻子完成了最后一次呼吸。”
我想,那一刻,格里高尔是解脱的。
杀死自己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格里高尔因家庭产生的自我仇恨。
格里高尔无法不仇恨。
这种仇恨既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
冷漠的父子关系滋生了冷漠的家庭关系,唯有利益在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或许是有真情的,但这种真情是由利益关系带来的。
格里高尔无法成为父亲出色的儿子,却可以成为不谙世事妹妹的守护者,因为一定程度上,妹妹也是受父亲压制的一方,他们有着共同阵营的合作基础。
但是一旦格里高尔无法维系这种利益关系,无法保证妹妹无忧无虑的生活,无法提供同一阵营的有用价值,就成了没用的人。
自然真情便被消磨,被妹妹抛弃。
这种应该极其亲近的人际关系,最后却变得异常冷漠,应该给予现实生活中的父子关系以警戒,父亲诋毁式教育最终毁灭的不仅是儿子,也是整个家庭。
本琼森曾这样形容父与子紧张的关系:“他们彼此站得太近,阴影扼杀了成长”。
卡夫卡的一生就是这样,他一辈子都处于父亲阴影之下,对父亲既依恋,又畏惧,无法拥有正常的现实生活。
他只活了短短41年,却三次订婚三次退婚,他的感情一片荒芜,难以支撑着新的家庭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