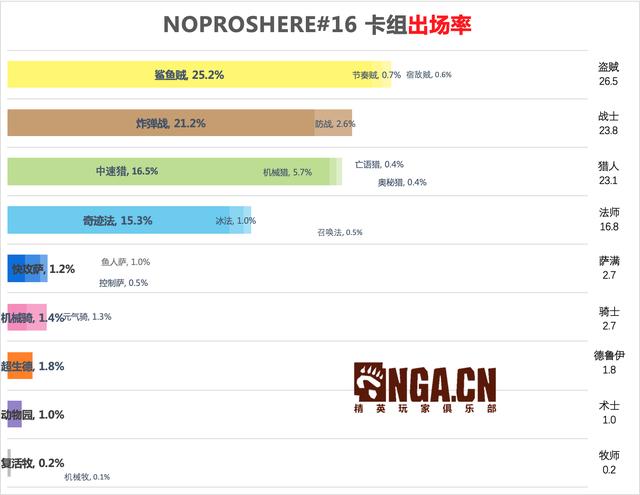马尔克斯(东方IC/图)
“一道血线从门下涌出,穿过客厅,流到街上,沿着起伏不平的便道径直向前,经台阶下行,爬上路栏,绕过土耳其人大街,右拐又左拐,九十度转向直奔布恩迪亚家,从紧闭的大门下面潜入,紧贴墙边穿过客厅以免弄脏地毯,经过另一个房间,划出一道大弧线绕开餐桌,沿秋海棠长街继续前行,无声无息地从正给奥雷里亚诺·何塞上算术课的阿玛兰妲的椅子下经过而没被察觉,钻进谷仓,最后出现在厨房,乌尔苏拉在那里正准备打上三十六个鸡蛋做面包。”
范晔读《百年孤独》时,就觉得书中这个场景富有画面感和镜头感。后来他成了小说的译者,仍然兴奋和好奇,这部文学经典的众多场景将如何呈现为影视语言。
据《纽约时报》报道,网络流媒体播放服务商网飞(Netflix)近日宣布,《百年孤独》将改编为西班牙语电视剧。小说自1967年出版以来,首次确认影视改编。
不少人争取过这部作品的影视改编权,但被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一拒绝。他和经纪人甚至以高价阻拦,将版权费从100万美元提升到300万美元。马尔克斯曾向《巴黎评论》杂志表示,自己会阻止《百年孤独》拍摄电影,理由是:“我希望在读者和作品之间保留一种私人关系。”
改编影视作品会不会破坏原著,历来是各界争论不休的话题。经典“能够经受起一切的解读,包括影视的改编也是一种解读”。范晔并不担心《百年孤独》的经典地位会因改编而被破坏:“还有一个特质,一切解读都不能穷尽它,你不能说哪个改编得再好,就真正完完全全地把原著复现出来了,或者看完这个完全就不用看原著了。”
网飞获得《百年孤独》的影视改编权,得益于其西班牙语作品如电影《罗马》和剧集《毒枭》的反响均不错。在第91届奥斯卡,《罗马》拿下了最佳导演、最佳外语片和最佳摄影三项大奖。
在马尔克斯之子罗德利亚·加西亚的印象中,父亲从前就和他人讨论是否要卖掉《百年孤独》的影视改编权。如今,加西亚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对我和我的母亲、兄弟来说,都合上了生活中旧的一章,翻开了新的一章。”他和叔叔贡萨洛·加西亚将担任该剧的制片人。
人物关系之复杂,给各国读者阅读《百年孤独》制造了巨大障碍。音乐人高晓松曾提到,小时候读《百年孤独》时列了一张大表格,专门标记人物关系。“从一个家族开始,两个儿子开始怎么怎么分下去,最后人越来越多……”影视改编的消息传来,有网友感慨:“终于可以靠脸把人给分清楚了。”
高晓松一度也弄不清楚马尔克斯为什么要这么写人物。《百年孤独》中许多人物的名字差不多,如奥雷里亚诺二世、奥雷里亚诺三世……等长大后再读,他才明白马尔克斯的用意。“作者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描述这是一个多少年来没有变化的小镇,一切仿佛都一成不变,但是在岁月变迁中。大家的生活如何变得支离破碎……”他写道。
从“马贡多”到“马孔多”《百年孤独》在中国的影响尤其深远。
1995年,范晔成为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上大学后,他第一次接触《百年孤独》,那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由吴建恒译自西班牙文的版本。五年后,他收到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的邮件。对方已经购买了小说的中文版权,正寻找译者,询问范晔是否有兴趣。
这时,《百年孤独》已经影响中国十余年。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至少出现了三个译本。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则回忆:“凡是作家,没有不读《百年孤独》的,文学青年们奔走相告,新华书店门口排起了长队。出版了多少个版本很难估量,但数量上保守估计是在几百万册,乐观一点甚至上千万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版本,由黄锦炎、沈国正和陈泉同三位译者共同翻译。1980年代读者的需求异常旺盛,为赶进度,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常由多名译者共同翻译。为求风格统一,黄锦炎最先确定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方法:人名均不超过四个字,地名用西语音译。这个版本里的小镇叫“马贡多”,范晔后来则依照拼音规则译为“马孔多”。
如今在网上搜索上海译文版《百年孤独》,基本上被炒到100元以上。但1984年底,正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的莫言,只花了1.6元,便在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了一本。
然而,这些版本全部都是“盗版”。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称,1990年代马尔克斯来访中国,发现书店里摆满没有获得自己授权的中译本《百年孤独》时,愤怒地表示有生之年都不会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
1992年,中国成为旨在保护版权的《伯尔尼公约》第93个成员国。外国文学译介、出版一度受到影响,但盗版现象没有根除。未获马尔克斯授权的中译本《百年孤独》依然流传,而且各个版本之间相互抄袭,被调侃为“汉译汉”。
从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译林、上海译文及人民文学社等多家出版社通过各种渠道试图获取《百年孤独》的中文版权。他们联络了马尔克斯本人、哥伦比亚驻华使馆,甚至墨西哥驻华使馆,但均未成功。直到2011年,西班牙语首版44年后,由新经典引进、范晔翻译的正版《百年孤独》终于出版。《百年孤独》的版权费用一直是业界之谜,传言中的金额往往超过百万美元。
他从未承认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提及拉美文学标志性的魔幻现实主义时,范晔马上纠正:“一说拉美就称魔幻现实主义,这可能是一个偏见,或者是刻板的印象。”
这个词汇,在许多年里都伴随着《百年孤独》。
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第一次将“魔幻现实主义”概念引进中国。文中陈述了《百年孤独》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但意在批判苏联对马尔克斯及其《百年孤独》的“吹捧”。这个时候,它还被称为“魔术现实主义”。
1979年,在林一安的文章《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盖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中,马尔克斯及其作品在中国获得正面评价。“魔幻现实主义”一词也正式成型,并得到沿用。
范晔在无数场合听到“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他的老师们从1990年代便开始推动对拉美文学的全面认识,但声音似乎比较弱小,没有带来太多改变。“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概括整个拉美文学的全貌,不管是1960年代、1970年代,还是现在21世纪。”他认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术语是标签化的,“它只在文学史上特定的阶段有一些影响,或者是批评界使用的术语”。
马尔克斯“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说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范晔说。
随着这个名词定型,1970年代末,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的黄锦炎读到了《百年孤独》的原文。小说是去古巴进修的同事带回来的,他“一拿到书就觉得放不下来,读完了就想把小说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久,他与同事沈国正一起选译六章,登载于《世界文学》杂志,成为国内最早发表的《百年孤独》译文。1984年,沈国正又送给朋友吴建恒一册汉译《百年孤独》,为云南版埋下了伏笔。彼时,这本小说在中国声名日隆。
“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早十年,或者晚十年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能他对中国的影响就没有这么大。”范晔认为,马尔克斯获奖的时间点,使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此巨大。
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进入中国。范晔提到,比《百年孤独》早一点或者晚一点,但不逊色于它的拉美文学作品有很多,但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不及。
此前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作家贾平凹曾谈到,1980年代外国文学涌进中国,令年轻人突然眼界大开。“对于作家来说,确实是一个好事情。让作家的思维发生变化了,他思考的问题,更大的问题,文学上的视野,扩大到世界上。”
书买回去,莫言看第一页的内容就异常惊喜,惊叹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但他心中也暗暗不服,自己生活中本有更丰富的故事,也可以写出这样的小说。于是,他提笔写出两篇:一篇模仿小说中的魔幻内容,写一个老人在自己身上贴了许多羽毛,幻想自己能飞起来;另一篇小说《金发婴儿》则模仿了著名的“多年以后”“许多天之后”等句式。
1984年底,在被视为“寻根文学”肇始的“杭州会议”上,与会作家、批评家就多次提到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1988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出版,收入了莫言、韩少功、扎西达娃等作家的作品,他们也常被冠以“寻根文学作家”称号。
范晔援引评论家说过的“隔壁的张老三成了万元户”,来解释马尔克斯对中国作家造成的影响。“同样是第三世界的国家,能够得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个好像全球承认的奖项,对中国作家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激励。”范晔说。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也将他与马尔克斯相比,认为“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
《百年孤独》的确具有国际影响,目前被翻译成46种语言,出售量超过五千万册,一直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作。
好像幻想成真,好像小说世界2014年,范晔参观了马尔克斯念书的学校,去了作家结婚的教堂。在马尔克斯家乡的小镇,即小说中马孔多镇的原型,他发现马孔多河边上有很大的白色卵石,和《百年孤独》里开篇写的一样,“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照相时,他还看到,一只很大的蚂蚁爬来爬去,对应到小说中的细节,“好像是幻想成真的东西,好像你走进了小说的世界”。
旅行沿着马尔克斯的生命足迹展开,范晔发现这位作家也是一位影视爱好者。改编影视作品时,马尔克斯往往担任联合编剧,诸如《俄狄浦斯市长》《寡妇蒙蒂尔》《爱与群魔》。他严肃地考虑过,要做一名编剧。
对于影视改编,马尔克斯不在意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他最在意细节。“他非常关心那个人物戴眼镜,用的道具是什么,看重这些细节。”范晔发现。
影像将如何表现《百年孤独》的那些文学细节,也令范晔好奇和期待。“有些地方是比较细节的,我觉得以影视语言不太好表现,反而是纯文字部分更能产生效果。比如这个上校一生打过多少次仗,受过多少次暗杀,也给人很大冲击,但更多的是文字的效果。”范晔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
成名之后,马尔克斯与朋友在古巴创建了一所影视学校,办过剧本写作班、工作坊。范晔购买过他的教材,“他是个内行,非常热爱影视这门艺术”。
作家还有过导演梦。马尔克斯在1987年告诉《拉丁报》:“导演曾是我青年时代的梦想,但现在我必须说,我永远不会导演电影,因为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我会是一个失败的导演。”他一生只与人合导过一部29分钟的实验短片《蓝色龙虾》。片如其名,那大致是一个秘密特工的故事,他的任务只是调查加勒比小城出现的蓝色龙虾。
马尔克斯的另外两部经典之作《霍乱时期的爱情》和《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都被改编为电影,他对改编大体满意。中国导演李少红的电影《血色清晨》,亦取材于后者。
至于《百年孤独》,马尔克斯有自己心仪的导演。他在1990年与日本大导演黑泽明面谈过,可惜并未具体讨论《百年孤独》的改编事宜。后来也有制片人想联系黑泽明执导《百年孤独》,但导演去世了。倒是在上映于1984年的影片《再见箱舟》中,日本导演寺山修司取用了小说的部分情节,他把故事背景挪到了偏远的日本山村。
“在电影中要表达你真正想说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我仍想着要做电影,但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种奢侈。”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马尔克斯形容,“我和电影的关系就像是一对夫妻,一对既无法分开住却也无法住到一起的夫妻。”
《百年孤独》终于要完整地影像化时,马尔克斯已经去世近五年。这次改编是否令他满意,将是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