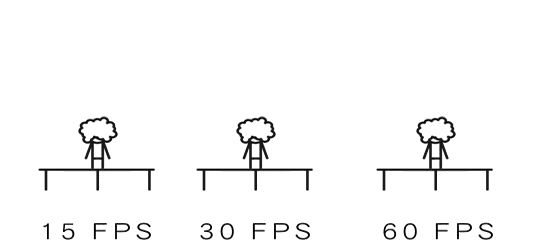文/李桂珍
寒风乍起,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又在大街小巷响起,那浓重的银川口音,那尾音长长的吆喝,听起来是那麽熟悉,却又遥远,只听那声音就象有蜜从中流出。
我从小就是在这吆喝声中长大的。
老银川的人都知道,70年前,银川北门有一家李家糖坊,门脸不大,但做出的糖却以酥、脆、甜而远近闻名,那就是我爷爷李孝开的。
从我记事起,就总见一家老小在热气腾腾的糖坊忙来忙去。
听爷爷说,这套制糖工艺是祖上传下来的,制做起来非常考究。
先说粗加工做糖坯,将碎白米和稗子米淘干净,上笼用旺火蒸热出锅,用木勺挖出来放在小盘内,掺入发好的大麦芽,大麦芽须洗净后,放在盘里盖上沾布,放在热炕上催其发芽,芽长两寸长后,将其收出放在碾台上碾碎铲起待用。
然后,用一小缸将蒸热的米放上,再放六木勺大麦芽,用炒板搅匀,再加一大锅开水,然后再搅匀。
缸的下面要铺上扫帚苗(靡子的杆),缸的下角有一个洞,事先要用麻拧成的塞子塞好。
发酵一个时辰后,待缸中冒泡即好。然后,将塞子拔掉,让糖水流入一个大盆内,将糖水倒进一个大铁锅,灶底加炭火,迅速翻炒,炒至糖水发粘,呈金黄色的糊状,然后用抹过油的木勺迅速将糖稀舀起,倒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让它自然冷却,这样糖坯就做好了。
精加工分四个程序,焐糖、炒糖、拉糖、切糖。焐糖就是将放凉的糖坯放在撒了米粉的毡上,(米粉要专门制作,把碎白米泡后,放在缸里捂一天,在碾子上碾碎过筛既得)放在烧烫的火炕上捂至发软。
炒糖就是将糖坯放在锅里用文火炒至可以拉成条状时,迅速出锅。
拉糖时,屋里温度要达到28度,湿度要有45度,有点蒸桑拿的感觉,由两个人面对面用特制的木板将糖坯拉成条状,动作要快,重叠的次数越多,中间的空隙越大,糖越脆。待糖呈奶白色,有二指宽,即可放在糖案上。
切糖就是用糖刀将微晾的糖切成三寸长的小段,码到糖盘里,放到门外冻上。
切糖的时辰特别关键,早了糖沾刀,不成型,晚了,一切糖就碎了。
切糖最显手艺,通常是由爷爷亲自操刀。
爷爷右手拿刀,左手拿着糖尺,眯缝着双眼,精心的量,小心的下刀,就象在做一件艺术品。
每当一根呱呱糖切完后,不多不少正好,不留一点边角料时,爷爷的脸就象一朵盛开的菊花。
1955年李家糖坊家人合影前排右3为爷爷李孝
豆瓣糖的制作很复杂,先将黄豆泡去豆腥味,煮熟捞出后控干,放在铁锅里用小火来回拨拉,待豆子呈金黄色,铲出放在糖案上压成两瓣,用筛子将碎块筛出,只用两瓣的。
然后,迅速将拉开的瓜瓜糖坯放在豆瓣上,待糖坯发热,将豆子全部沾在糖上,用糖板将其压制成形切块装盘,放在门外冷冻即成。
此外,制作的品种还有面糖、灌心糖、牛皮糖等等。
一般做糖从新稻米下来开始,到来年四月为止,其余时间天太热,糖做好就化了。
做糖对水的要求特别高。
北门城楼附近有一口甜水井,水质甘甜清澈,水量特大。
我和姐姐长到八九岁,就开始抬水,记得两只大木桶快到我的肩膀,扁担又粗又重,每天放学后,都要抬两趟水。
出完糖水的糖渣很有用,喂得猪又大又肥。
糖渣人也可以吃,低标准时,糖渣救了我们全家的命。
后来,李家糖坊参加公私合营,爷爷开始给公家做糖,存在了六十多年的李家糖坊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还在。
六四年前后,牛奶糖以其物美价廉的优势占领市场,合作社倒闭,爷爷失业在家,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消失了。
改革开放了,满春乡搞多种经营做糖,请爷爷当师傅,爷爷起早摸黑,劲头十足,于是,寂静了十几年的吆喝声又在大街小巷响起。
那年,爷爷七十多了,每天顶着星星上班,背着月亮回家。
我每天晚上在昏暗的街灯下,边玩跳方边等爷爷回家。
一天晚上爷爷没回来,第二天清晨,在上学的路上,我碰到了爷爷,只见爷爷穿着一身黑棉衣裤,两只胳膊向后抄在袖筒里,栽绒棉帽的耳朵呼闪着,脖子向前梗着,头一点一点地向家走着,呼出的热气在帽子上结成了厚厚的白霜,就象一个圣诞老人。
尽管爷爷这样卖力,但不到一年,爷爷还是被辞退了,原因是爷爷做糖一招一式都要坚持原来的工艺,费时多,成本高,糖的价高了又卖不出去,厂子要维持下去就要偷工减料。
爷爷坚决不干,发生争执,爷爷只好回家。
失去手艺的爷爷是苦闷的,他常常坐在院子里,两眼发呆,拿着那把磨的油亮的糖尺在手上打,那啪啪的声响在寂静的院子上空回响。
他的嘴里喃喃的不知说些甚麽,任由夕阳将金色的余辉洒遍全身。
我知道,李家糖坊手艺的失传是爷爷心中永远的痛。
父亲退休后闲不住,凭着依稀的记忆开始做糖。家里地方小,又没大缸,就将做糖的熬糖程序省了,直接买来糖稀做。
糖稀基本都是玉米熬制的,也很甜,但总带一股酸味。后来,民间做糖的工艺基本如此。
好在现在的小孩吃得都是这种糖,以为豆瓣糖、呱呱糖就是这个味。
我想,只要每年在寒风乍起时,能响起豆瓣糖、呱呱糖的吆喝声,爷爷就会含笑九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