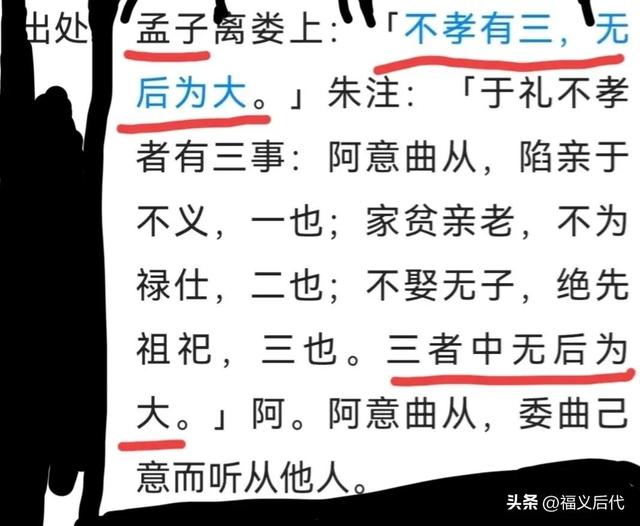一、太史公的自我期许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1]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人的作品。[2]《史记》不是一部合乎今日标准的“历史书”,虽然它在客观上为我们提供了史料,但太史公写作《史记》的目的不是叙述历史。《史记》“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追寻某种意义,“述往事”是“思来者”的手段,也是载体。一如司马迁在《自序》中引用董仲舒所说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表面上只是述“行事”,而孔子所作“空言”恰在其中。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张(作),也蕴涵在《史记》对古今史事的叙述中(述)。
从司马谈到司马迁,都有一种“述作”的使命感。《自序》司马谈临终前执迁手而泣曰:
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
司马谈认为周公的伟大在于歌颂前人功德,孔子的伟大亦在于编修以旧闻为载体的“六经”。
司马迁当仁不让,自诩为继承周公、孔子的人: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而司马迁继承孔子的方式,是希望通过写作《太史公》书来继承孔子所作《春秋》,孔子编修的“六经”是其重要依据。可以说,继《春秋》,是太史公的自我期许。
就像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一样,司马迁也矢口否认自己要“作”一部类似《春秋》的书,称自己只是“述故事”,“非所谓作也”。然而实际上,《史记》全书引用和比附《春秋》之处比比皆是,[3]何况《自序》下文立即自道《太史公》书记事的起讫:
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麟止”正是比附《春秋》绝笔。
有趣的是,对于《史记》记事的上限,司马迁为何不效法他认为是孔子所编籑的《尚书》,始自“陶唐”,[4]而一定要“自黄帝始”?这是我们阅读《五帝本纪》时,需要始终思索的问题。
二、五帝人选的取材
《史记》的篇目次序往往有一番用意。太史公把《五帝本纪》置于首篇,把黄帝冠于五帝之首,其中的深意值得发掘。从其所“述”发掘其所“作”,是一件困难的事。必须兼具“好学”、“深思”的品质,若“寡闻”、“浅见”则不得“心知其意”。[5]要理解太史公,必须好学博闻,掌握比《史记》更丰富的信息。本文正是通过史源学的方法,意即分析《史记》面对丰富而芜杂的“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材料),[6]作了怎样的取舍和裁断(取、裁),从而发掘太史公的思想和主张(作)。
《五帝本纪》中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一组五帝人选,在太史公的时代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比如收入《礼记》的《月令》,所载五帝是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挚)和颛顼,《系辞》记载的五位上古圣王是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太史公为什么不选择《月令》或《系辞》的五帝版本,而选定了目前这一组五帝,他的文献依据是什么?
太史公在《五帝本纪》赞语中,对史源有明确表述:
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太史公指出除《尚书》以外,《五帝德》和《帝系》是《五帝本纪》最重要的史源。至于为什么相信后来收入《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太史公给出的理由有三:第一,认为这两篇文献是孔子所传。第二,实地考察相传为黄帝、尧、舜活动的区域,与这两篇文献有相合之处。第三,可与《左传》、《国语》相发明。
《史记》五帝取材于《五帝德》和《帝系》,然而太史公给出的解释并不能解决我们对于五帝人选的疑惑。如果说《五帝德》、《帝系》与孔子有关,虽然这并非儒家的共识(“儒者或不传”),可是太史公同样认为《系辞》与孔子有关,[7]为何不取《系辞》五帝?此其一。太史公实地考察了黄帝、尧、舜的遗迹,为什么不考察颛顼和帝喾的遗迹?[8]而《史记》五帝人选的特殊之处,除了以黄帝为始,主要就在于颛顼和帝喾,黄帝、尧、舜作为五帝则争议不大。此其二。《史记》五帝并非《五帝德》和《帝系》专有,先秦文献如《国语·鲁语下》、《吕氏春秋·尊师》、《管子·封禅》也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并举,[9]唐人所见《世本》五帝原亦如此,[10]太史公为何重点谈《五帝德》、《帝系》,《国语》只处于从属地位,且未及《世本》、《管子》?此其三。[11]由此我们认为,太史公看重《五帝德》和《帝系》,不是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可信的五帝人选,而是因为它们赋予了五帝某些特质。
三、对《帝系》的吸收
与《月令》、《系辞》、《吕氏春秋·尊师》等文献中的五帝相比,《五帝德》、《帝系》最明显的特点是,以黄帝为始。更重要的是,在《五帝德》尤其是《帝系》中,五帝中的后四帝,乃至夏、商、周三代的始祖禹、契和后稷,全是黄帝的子孙。
建构远古帝王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是《五帝德》和《帝系》的独创。比如《国语·晋语四》即谈到“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但是《五帝德》尤其是《帝系》,首次建构了一整套由五帝至三代的血缘谱系,使五帝同源,三代一系,皆出于黄帝。比如舜的出身,《孟子》只说“舜发于畎亩之中”,本来是匹夫,父亲是瞽叟,并未指出瞽叟以上的血统。而《帝系》把舜的血统清清楚楚地追溯到颛顼乃至黄帝。《史记》全盘吸收了这套尚未成为共识的血缘系统,记载于《五帝》和《夏》、《殷》、《周本纪》及《三代世表》等篇,深刻地影响了此后两千年的文明认同。尤其是作为十表之首的《三代世表》,所以将五帝、三代帝系集于一表,并巧妙地采用“旁行斜上”的体裁,正是出于对这一谱系的完整呈现。[12]
为了维护这一血缘谱系,《史记》对它可能引起的质疑加以解释甚至弥缝,在此聊举三处。帝喾是颛顼的侄子,何以继颛顼之后为帝,《五帝本纪》解释说帝喾的父祖玄嚣、蟜极“皆不得在位”。此其一。对于舜的出身,《五帝本纪》解释说舜的祖先从颛顼之子穷蝉以下,“皆微为庶人”。此其二。同为帝喾之子,尧何以成为五帝之一,而挚不列入五帝。《五帝本纪》说:
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
挚是尧的哥哥,理应继立为帝,[13]此处却说他“代立”。“代立”一词在《史记》中多次出现,我们把它视为一种太史公“书法”,在这里指挚作为帝是“不善”的,[14]不称其位,所以不能列入五帝。此其三。反观前两处“不得在位”和“微为庶人”,措辞也是有微意的。前者暗示帝喾有“在位”的合理性,后者告诉我们舜这一支早已是匹夫了,因而用语有别。我们认为以上三处细节,都是太史公对《帝系》五帝、三代血缘系统的辩护,而未必有史料上的依据。
《史记》坚持这一套宏大的血缘谱系,认为五帝、三代血缘出于黄帝,这无疑是《史记》记事以黄帝为始的重要原因。至于五帝人选是否有颛顼、帝喾,可能只是这一血缘谱系的副产品而已。
对古人而言,五帝人选相当于历史事实。然而太史公裁断这一史实所依据的,并非材料的客观性,而是自己心中的准则。太史公为何对五帝、三代的血缘谱系情有独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五帝事迹乃至整部《史记》。
四、对《五帝德》的增删
《五帝本纪》记述黄帝、颛顼、帝喾的事迹(述),主要取材于《五帝德》(取)。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太史公删削和增添的一些内容(裁),可能包含了他的思想和主张(作)。
需要说明的是,太史公看到的典籍内容与今本一定有所不同。我们利用现存典籍分析《史记》取裁,只能作有限度的讨论。然而当《史记》与今本典籍的若干差别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同一问题时,应承认该问题确实在太史公的考虑之中。
(一)人帝
今本《五帝德》记载黄帝“乘龙扆云”,[15]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而这些神异的事迹都被《五帝本纪》删去。太史公似乎在向读者强调,黄帝、颛顼、帝喾等五帝,都是人帝。虽然《五帝德》本来就认为黄帝更近于人,[16]太史公仍然删去了可能引起误会的内容。
与此相关,《五帝德》含混交代黄帝寿命大约是一百岁,而《五帝本纪》明确记载了黄帝的死,说“黄帝崩,葬桥山”,最终如其他常人一样死去,埋葬在了一个确定的地点。[17]
与《五帝本纪》塑造的黄帝形象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封禅书》方术之士口中的黄帝。前者是人,后者是仙,是不死的。[18]汉武帝所以汲汲于封禅,其目的之一即在于长生不死。为了达成封禅的条件,武帝刻意营造太平盛世。而在这种虚假的繁荣背后,民生凋敝,盗贼蜂起。[19]武帝太初改元诏更是直言“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20]似乎有鉴于此,太史公着意在全书首篇,塑造黄帝作为人帝的形象。
《五帝本纪》赞语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太史公写作《五帝本纪》时,面对五花八门的黄帝故事,如何取舍和裁断?其标准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一定寄托了太史公的理想,而其理想正具有现实指向。司马迁所谓“上记轩辕,下至于兹”,[21]所谓“通古今之变”,[22]《史记》中的“古”往往与“今”相呼应。此类微义,非“好学深思”的“圣人君子”不得“心知其意”。[23]在此意义上,《史记》与《春秋》一脉相承。
(二)战争
《五帝本纪》所载颛顼、帝喾事迹,主要来自《五帝德》。而黄帝事迹,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不见于今本《五帝德》。最引人注目的,是开篇对战争的叙述: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
除了“治五气”至“然后得其志”,其余均非今本《五帝德》所有。
《史记》作为一部崇尚“六经”、自命继《春秋》的书,竟然以战争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全书的序幕。《五帝本纪》记述黄帝发动战争,达四处之多,只有第二处阪泉之战沿用了《五帝德》。综观全段,黄帝开战的次序值得玩味。先是针对不服从当今天子炎帝的诸侯用兵,致使诸侯宾从炎帝。需要注意的是,“神农氏世衰”中的“世”,指的是王朝、家族的衰落,而不单指炎帝这一任统治者。这次战争好比在王室衰微的东周,伯主作为诸侯之长,尊奉周天子,主持秩序。
其次对失去诸侯拥戴的炎帝发动阪泉之战,结束了业已衰落的神农氏的统治。此次战争,或可类比秦灭周。
接下来的涿鹿之战始针对蚩尤。上文说“蚩尤最为暴”,此处又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并非赘余。阪泉之战以前,蚩尤不服从的是炎帝。阪泉之战以后,神农氏的统治告终,蚩尤作乱,轩辕责无旁贷。这里的“帝命”,应指黄帝,下文对轩辕的称谓即已变为“黄帝”。打败“不用帝命”的诸侯蚩尤之后,黄帝受到所有诸侯的拥戴,无论实质上还是名义上,都成为了独一无二的天子。此次战争,与楚汉战争有类似之处。
黄帝最终成为天子,建立新王朝(有熊),此后的战争,是为了征讨不服。类似汉高祖对异姓诸侯王的战争。
这些对战争的叙述,反复提及“诸侯”。根据今天的历史研究,诸侯“宾从”和贡“享”天子,是西周封建乃至秦汉大一统王朝的产物,炎黄时代的国家形态绝非如此。《史记》的类似记述,是将太史公当代的制度和文化套用在了古代,违背了历史事实。虽然太史公对古史的认识存在这样的局限,但并不妨碍我们解读太史公的意图。我们认为,用诸侯的归附和离散来表达民心所向甚至天命去就,[24]是遍布《史记》全书的一种“书法”。在阪泉之战前,“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意味着天命已在轩辕而不在神农氏,“轩辕乃修德振兵”,这与《史记》记述桀、纣末年的情形如出一辙。[25]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始践帝位。
《史记》对黄帝用兵、汤武革命直至秦崩楚亡的易代战争,相关叙述都带有天命论的色彩,即所谓“易姓受命”,甚至秦灭周、统一六国亦然。[26]太史公认为得以结束旧王朝、创立新王朝的战争,是正义的,是顺应天命的。他在《律书》中指出: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中略)。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27]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需注意此处的“胜者用事”,带有五德终始的色彩,并非“胜者为王”之意。
从《史记》战国秦汉部分看来,太史公抱持一种“逆取顺守”的理念,守成要用文治,但易姓换代,势必要通过轰轰烈烈的战争才能迎来新的时代,就像汉高祖所做的那样。
汤武革命、易代战争在《孟子》中已有很多讨论,到了太史公的时代,却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原来在汉景帝时,儒家《诗》学宗师辕固生与道家黄生,[28]争论汤武是受命还是臣弑君。处于下风的辕固生最后抬出了高皇帝,惹得景帝禁言,“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29]太史公无疑是赞成辕固生的,辕固生所说:
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
与《孟子》一脉相承。太史公也将这种论调,具体地落实到全书的易代战争中。比《孟子》走得更远的是,《孟子·尽心下》说武王伐纣“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认为《尚书·武成》的血腥记载于理不合。而《史记》完全不回避对武王斩纣的记述,后来遭致极多非议。大约在太史公看来,从黄帝、汤武至刘邦这些受命帝王,不应以常人的道德伦理来衡量。《五帝本纪》开篇即不满足于《五帝德》等文献中既有的黄帝形象,着意通过繁复而周密的战争叙述,重塑黄帝的伟大形象,突出易代战争的正当性。
然而与其他朝代鼎革不同的是,舜、禹之间易代,乃是通过禅让而非战争,我们应如何认识夏的建立?同时,五帝易代,均为和平过渡,也不是通过战争,[30]是否意味着太史公将五帝视为同一王朝?要回答这些问题,应先厘清“易姓受命”在《史记》中的意涵。下面我们通过《五帝本纪》对姓和国号的论述,推测“姓”在王朝更迭中可能具有的意义;再通过《史记》对《尚书》、《孟子》禅让故事的取裁,观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论。
五、对《国语》的化用
(一)同姓则同德
《五帝本纪》末尾有一段关于姓和国号的论述:
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
此处将夏后、商、周三代与五帝的有熊、高阳、高辛、陶唐、有虞一样,都视为“国号”,可知在太史公看来,五帝像三代一样,是五代王朝。同时,太史公认为五帝和禹皆为同姓(公孙),禹建立夏朝后改姓,三代异姓。
本文无意根据今天学界对姓氏的研究,纠正太史公在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存在的偏差,我们关注的是太史公为姓赋予的意涵。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太史公对五帝及禹的姓及国号的特殊看法,与《五帝本纪》叙述这六代王朝更迭时均未发生易代战争冥合。我们大胆推测,太史公认为只有在“易姓”受命的改朝换代中,战争才是必要的。而这一理论的来源,似乎是《国语》。
《五帝本纪》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学者常常用来讨论姓的起源: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这句话出自《国语·晋语四》。今本《国语》原文作:
司空季子曰:“同姓为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下略)。”
司空季子这番话的落脚点是同姓不婚、异姓则可以通婚,以此来说服晋公子重耳娶晋怀公的前妻、秦宗室女怀嬴。对比《五帝本纪》对姓的论述,实与司空季子的言论有很多出入。差别较大的如司空季子说黄帝和炎帝是亲兄弟,黄帝是姬姓。而《五帝本纪》黄帝姓公孙,“神农氏世衰”,意味着炎帝与黄帝属于不同的家族,不可能是兄弟。
小有异同的,比如司空季子说黄帝之子只有青阳和苍林氏两人与黄帝同姓。关于黄帝之子,《五帝本纪》承袭《五帝德》和《帝系》,只提到了玄嚣和昌意两人,后四帝及三代始祖,全是玄嚣、昌意这两支的子孙。《五帝德》和《帝系》未明言五帝的姓,《五帝本纪》既然说从黄帝到舜、禹同姓,那么玄嚣和昌意也应该与黄帝同姓。《五帝本纪》又说玄嚣就是青阳,正好与《国语》相合,而昌意则与《国语》苍林有所不同。[31]
《五帝本纪》跟《国语》的相同之处,看起来只有“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如果我们暂时搁置黄帝姓什么、黄帝的儿子姓什么这类事实判断,思考太史公和司空季子认为“姓”意味着什么,那么二者似乎尚有更深层的共通之处。司空季子说“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并认为炎、黄开战与异姓异德有很大关系,“姓”可以对现实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史记》全书记载的“易姓受命”,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战争,正与“异姓则异德”相合;而从黄帝至禹,按照太史公对其国号和姓的论述,属于同姓易代,则是和平交接,正与“同姓则同德”相合。
《五帝本纪》赞语说《国语》“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弗深考”者,大约是指黄帝姓什么、黄帝与炎帝有无血缘关系这类具体的事实判断,与太史公的判断不符。能够“发明”《五帝德》、《帝系》和“表见不虚”的,除了《鲁语下》提及的五帝人选,以及《国语》中其他一些关于上古帝系、族姓的论述与太史公的判断相符者,[32]“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的理论,亦当在太史公的考虑之中。
(二)旁证:易姓受命与改正朔
我们还可以从正朔的角度,为“同姓则同德”提供一个有力的旁证。《历书》说:
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似乎在说只有“易姓”的王朝更迭,才改正朔。
《史记》全书确实贯彻了这一理论。《五帝本纪》记载黄帝“迎日推策”,《历书》说“昔自在古,历建正作于孟春”,又说“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中略)各司其序,不相乱也”。太史公可以追溯的最早的历法是黄帝建立的,宜以孟春一月为岁首,即所谓夏正。《五帝本纪》备载帝尧“敬授民时”,亦与历法有关,而在《历书》的叙述中,颛顼命重黎、尧立羲和两事,都是对黄帝所建秩序的恢复,而非改历。《历书》又说尧禅舜、舜禅禹,皆申诫“天之历数在尔躬”,乃是强调历法。玩《历书》文意,“历数”应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的,并未新建,《五帝》、《夏本纪》亦未载舜、禹修历之事。[33]所以《历书》提出: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
中国文明只应交替使用三正。太史公大约认为,黄帝至夏六代均建寅,商、周则因易姓受命而改正朔,秦、汉易姓受命,亦当改用三正之一。[34]
太史公的这一理论,背后有经学家对于五帝是否改正的分歧。一说认为:“惟殷周改正,易民视听,自夏已上皆以建寅为正。”[35]一说认为:“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尧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时未改尧正,故云‘正月上日’;即位乃改尧正,故云‘月正元日’。”[36]虽然我们见到的两说都晚于太史公,但《历书》所述与前说若合符节,而《五帝本纪》删去其史源《尚书》尧死后“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的记述,又恰与后说针锋相对,由此可以断定,这两种《尚书》经说由来已久,是太史公“厥协六经异传”的内容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较之可能是《历书》史源的《诰志》和《国语》“绝地天通”条,《历书》改《大戴礼记·诰志》“虞夏之历”为“昔自在古”,并新增“盖黄帝考定星历”云云,从而令《诰志》“历建正作于孟春”和《国语·楚语》颛顼命重黎“绝地天通”,得以巧妙地上溯至黄帝。《历书》对《诰志》和《国语·楚语》的缀合与加工,似乎正是太史公对黄帝至夏均建寅的辩护。
至此,我们发现了《史记》中易姓受命与改正朔的相关性。其逻辑正与易姓受命和战争的相关性一致。意即易姓受命,必然伴随着流血战争;异姓王朝建立之初,一定要改正朔,才能顺承天意。同姓受命,则是和平交接;同姓王朝建立,当沿袭前朝正朔。这正与《国语》“同姓则同德”、“异姓则异德”相合。
(三)五帝、三代帝系建构的深意
《史记》五帝三代的帝系、血缘、国号、姓、历法,共同营造了一个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史记》所以坚持五帝三代同出黄帝,所以认为黄帝至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所以认为易姓受命始改正朔,这些看似怪异的论调,其深意可能在于,太史公试图对黄帝以降的所有王朝更迭,获得一以贯之的认识。
既有的五帝史料诚然划定了叙事的界限,使太史公不得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但太史公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对文献施以有倾向、有目的的取裁是,[37]。明乎此,我们有望对《史记》的记载获得更丰富的理解。比如《五帝本纪》谓禹本来与五帝同姓、建立夏朝后改姓,或可视为太史公针对各项“史实”与诸条“理论”可能引起的矛盾,而使夏姓这一“史实”迁就“理论”和其他“史实”的弥缝工作。
鄙见容易引发的一个质疑是:舜、禹和平交接乃是由于禅让,与同姓异姓无涉。然而我们回到《史记》自身的脉络,会发现:政权能否成功交接,决定因素并非禅让还是世袭,而在于是否得天命。禅让应在受命的框架下加以认识。下面,我们主要通过《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中尧舜、舜禹以及禹启的政权交接,观察太史公的受命理论。
六、对《尚书》和《孟子》的拼接
关于历史上的“舜禹之事”,太史公一定看过很多“百家杂语”,例如《韩非子》“舜逼尧,禹逼舜”及“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一类的记载,但《史记》全未采信。
《五帝本纪》尧、舜事迹主要取材于《尚书·尧典》和《孟子·万章上》。《史记》记载尧在位时,舜得到四岳的举荐,并完美地通过了各种考验,尧对舜说“女登帝位”,欲禅于舜,这时舜是推让的,“让于德不怿”。[38]《史记》的这些叙述全部本自《尚书》。此后“正月上日,舜受终于文祖”,舜的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史记》加入了《尚书》原文没有的内容:
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
这句话有两层意涵。首先,舜还不是真天子,是暂时做代理天子。其次,舜是不是可以继位为真天子,不是尧个人能决定的,要看天命。
这两点在《史记》中非常重要,不仅在尧舜禅让、舜禹禅让、禹禅益而启继这三个事件中一以贯之,还影响到太史公对其他一些重大问题的叙述。[39]其实这两点都本自《孟子·万章上》:
咸丘蒙问曰:“(中略)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中略)。”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中略)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万章曰:“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中略)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中略)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中略)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
尤其是“万章曰”这一段,基本全为《五帝本纪》吸收。而在《尚书》经文中并不具备这些内容,[40]可以说是孟子的《尚书》学说。
《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史记》虽未出现这句话,实际上秉承了这一精神。尧虽然属意于舜,但最后使舜践祚为天子的不是尧,是天。天意又从何得知呢?这是贯穿《史记》始终的一个问题。《五帝本纪》在此与《孟子》完全一致,是通过诸侯的归附等现象来体现天命所属的。舜得天命,所以才能践天子位。舜禹禅让亦与此如出一辙。
可是后来禹禅益未成,启继禹为天子。这说明人类历史从“公天下”堕落为“家天下”了吗?《史记》中完全没有这种论调。[41]《夏本纪》用“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来体现天命在启不在益,此即《孟子》所谓“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启继禹,与尧舜、舜禹禅让的机理并无二致,起决定作用的是天命。
启得天命,还可以从太史公对《尚书·甘誓》的述作中得到印证。《夏本纪》叙述启即位后:
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启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中略)。用命,赏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则帑僇女。”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
从“大战于甘”到“予则帑僇女”与《甘誓》内容相同。然而《甘誓》本文并未交代是谁向有扈氏开战。《墨子》、《庄子》、《吕氏春秋》以及刘向《说苑》认为《甘誓》是禹所作。《史记》认为启作,乃是依据《尚书序》。《书序》原作“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史记》承袭此说,并进一步认为开战的原因就是“有扈氏不服”,质疑启的王位合法性。那么《甘誓》“天用剿绝其命”、“今予维共行天之罚”,在这一语境下就成为有扈氏违背天意,启要代天去惩罚他。如果说这还只是启的一面之词,那么最后《史记》新增的“天下咸朝”,恰恰表明在太史公看来,启是得民心、得天命的。
对于禅让和世袭的优劣,《孟子·万章上》讲得非常明白:
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
《史记》秉承了这一精神,并不鼓吹禅让。无论禅让还是世袭,都不能脱离天命孤立看待。
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孟子的时代,燕国上演了活生生的禅让,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燕世家》记述当时的情景: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于子之。
《六国年表》说“君让其臣子之国,顾为臣”。其他很多世家、列传也有类似的叙述,强调君臣纲纪的颠覆。《燕世家》更是把燕哙禅让的动机说成是受了苏代和鹿毛寿的蛊惑。甚至还说:
孟轲谓齐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
太史公对燕哙禅让的完全否定,溢于言表。
《史记》对此的记述诚然与《孟子·公孙丑下》有不少出入,其思想和主张却是相通的。《史记》批评燕国昔日的国君变为臣下,正是前引《孟子·万章上》中“齐东野人”对尧、舜禅让的认识水平。更重要的是,《孟子》说“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同理,国君也不能仅凭个人意愿把君位指派给人。王位、君位不是任何个人的私产。
那么继体之君应如何确定?《史记》全书推崇嫡长子继承制,[42]似乎就是把血统视为一种天意。倘若太子缺席,诸侯或国人的意向则变得更加重要。
结语
通过观察《五帝本纪》对《五帝德》、《帝系》、《国语》、《尚书》等主要史源的取舍和裁断,可知《五帝本纪》凝结了太史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这些思考或多或少指向一个问题:王朝更迭。这也是贯穿《史记》全书的问题。旧王朝何以失天命,新王朝何以得天命,新王朝的历史定位是什么。这是太史公究天人、通古今,竭力思考的问题。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既非唐尧,[43]也非三皇。[44]太史公追求的既不是现成的信史,也不是单纯的古老。太史公看重的应是黄帝的典范意义。黄帝凭人力获天命,用战争创立异姓王朝,继而衍生五帝、三代。黄帝是太史公及后世的“圣人君子”,认识汉家从何而来时,沿秦、周而上,能追溯到的最悠久、最具典范意义的王朝开创者。
本文原载《文史》2020年第1辑(总第130辑)
向上滑动 查看注释
[1] 《太史公自序》谓“为太史公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太史公百三十篇”。两相参照,我们倾向于认为书名原作“太史公”。为了兼顾学界的习惯,本文统一标作“《太史公》书”。
[2] 本文在不区分司马谈和司马迁时,统称作者为太史公。
[3] 另一方面,太史公的见解与《春秋》不尽相同,否则何必另作《太史公》书。
[4] 据《五帝本纪》赞语,太史公应认为“《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书》缺有间”造成的。
[5] 见下引《五帝本纪》赞语。
[6] 《太史公自序》云:“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7] 见《孔子世家》。
[8] 今本《五帝德》载有颛顼的活动范围。
[9] 《封禅书》“管仲曰”云云历举十二位曾事封禅的古代帝王,司马贞《索隐》云“今《管子书》其《封禅篇》亡”,意即《史记》此处取材于《管子·封禅篇》。孔颖达《礼记正义·王制》引述《管子》云:“无怀氏封泰山,伏犧、神农、少皞、黄帝、颛顼、帝喾、帝尧、舜、禹、汤、周成王皆封泰山。”所引正与《封禅书》相近。
[10]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云“太史公依《世本》、《大戴礼》,以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又云孙氏注《世本》“以伏犧、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世本》已佚,王谟等人辑本或将黄帝列入三皇,是从孙氏注,非《世本》原貌。
[11] 更有甚者,《史记·历书》所言上古帝王无帝喾,有少皞,似与《五帝本纪》自相矛盾。究其原因,少皞乃沿袭《历书》此处的史源《国语·楚语》所述“绝地天通”事,与《五帝本纪》的五帝人选,并非同一系统。
[12] 《三代世表》的体裁,参赵益《〈史记·三代世表〉“斜上”考》,《文献》2012年第4期。
[13] 《史记》全书流露一种倾向,认为嫡长子继承制是自古就有的制度。
[14] 《史记索隐》云:“古本作‘不著’,(中略)俗本作‘不善’,不善谓微弱,不著犹不著名。”
[15] 《五帝本纪》不取《五帝德》黄帝“乘龙扆云”,而补入《左传》黄帝官名以云命、为云师的记载。学者解释《五帝德》的“扆云”,一说驾驭云,一说如《左传》以云纪事。
[16]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孔子“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孔子回答:“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孔子讲述黄帝事迹之后,说:“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
[17] 本文此处参考阮芝生先生《三司马与武帝封禅》,《台大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
[18] 参阮芝生《三司马与武帝封禅》。
[19] 见《平准书》、《酷吏列传》等。
[20] 见《历书》。
[21] 见《太史公自序》。
[22] 见《报任安书》。
[23] 《太史公自序》云:“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24] 对于诸侯的归附,《史记》的用语是诸侯“归”、“朝”等等;对于诸侯的离散,《史记》的用语是诸侯“去”、“叛”、“不至”、“不朝”等等。而在诸侯国内,则往往以国人共同的行为表达正当性。
[25] 《夏本纪》云:“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殷本纪》记纣时“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诸侯以此益疏”,“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等等。
[26] 《六国年表》序云:“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又云:“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
[27] 《律书》此处颛顼、共工之事,不见于《五帝本纪》,亦与《五帝本纪》的五帝系统不合。这种现象在《史记》中比较常见,我们认为太史公在不同的篇章使用了不尽相同的史源,没有强加整合和统一。
[28] 《太史公自序》谓司马谈“习道论于黄子”,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儒林传》曰黄生,好黄老之術。”
[29] 事见《儒林列传》。
[30] 在此以《五帝本纪》所述历史为讨论对象。
[31] 上古“昌”、“苍”同音,“意”和“林”差别较大。
[32] 参李零《帝系、族姓的历史还原——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史》2017年第3辑。
[33] 仅《夏本纪》赞语提及《夏小正》,但未明言夏朝所建。
[34] 对于建亥的秦历,太史公每有讥评。《历书》下文说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中略),而正以十月(中略),然历度闰余,未能睹其真也”,对秦历不以为然。同样的语气,在《封禅书》和《张丞相列传》中也有所流露。
[35] 《尚书·舜典》“正月上日”传《正义》引“先儒王肃等”说,《正义》并谓“孔意亦然”,伪孔传也持这种见解。
[36] 同上引郑玄说。亦见《五帝本纪》“正月上日”张守节《正义》引。
[37] 尤其能说明问题的是,《史记》春秋部分对《左传》和《公羊》的取裁。
[38] 据裴骃《集解》和司马贞《索隐》,《史记》的“不怿”采用了《今文尚书》“不怡”,《古文》作“不嗣”。
[39] 比如周公是否称王的问题。对此《尚书》家有相反的学说,太史公则认为周公摄政未称王。
[40] 伪孔传亦认为舜摄位。
[41] 以禅让为公天下的论调,与《史记》尧、舜、禹皆是黄帝子孙的血缘谱系相矛盾。
[42] 我们的理由有二。第一,太史公崇尚父死子继,否定兄终弟及。《史记》全书叙述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措词有明显区别,并暗示兄终弟及会导致衰乱,这在《殷本纪》中尤其明显。第二,因废嫡立庶而导致衰乱,在《史记》中不胜枚举。如《鲁世家》襄仲杀嫡立庶,哀姜哭市,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
[43] 《汉书·司马迁传》赞云“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批评《史记》尧以前非信史。
[44] 张衡批评《史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见《后汉书》本传注引《衡集》。后来司马贞《史记索隐》即为《史记》补作《三皇本纪》,记太皞伏羲、女娲、炎帝神农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