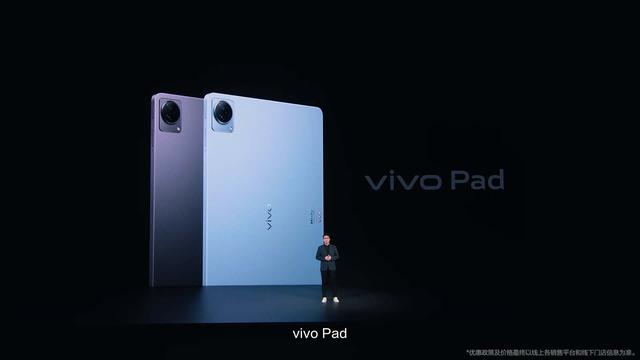不毁灭的背影文 | 沈从文,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沈从文最短一句话?我们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
沈从文最短一句话
不毁灭的背影
文 | 沈从文
“其为人也,温美如玉,外润而内贞。”
旧人称赞“君子”的话,用来形容一个现代人,或不免稍稍迂腐。因为现代是个粗犷,夸侈、褊私、疯狂的时代。艺术和人生,都必象征时代失去平衡的颠簸,方能吸引人视听。“君子”在这个时代虽稀有难得,也就像是不切现实。惟把这几句作为佩弦先生即朱自清,中国现代作家。身后的题词,或许比起别的称赞更恰当具体。佩弦先生人如其文,可爱可敬处即在凡事平易而近人情,拙诚中有妩媚,外随和而内耿介,这种人格或性格的混和,在作人方面比文章还重要。经传中称的圣贤,应当是个什么样子,话很难说。但历史中所称许的纯粹君子,佩弦先生为人实已十分相近。
我认识佩弦先生和许多朋友一样,从读他的作品而起。先是读他的抒情长诗《毁灭》,其次读叙事散文《背影》。随即因教现代文学,有机会作进一步的读者。在诗歌散文方面,得把他的作品和俞平伯先生成就并提,作为比较讨论,使我明白代表五四初期两个北方作家:平伯先生如代表才华,佩弦先生实代表至性,在当时为同样有情感且善于处理表现情感。记得《毁灭》在《小说月报》发表时,一般读者反应,都觉得是新诗空前的力作,文学研究会同人也推许备至。惟从现代散文发展看全局,佩弦先生的叙事散文,能守住文学革命原则,文字明朗、素朴、亲切,且能把握住当时社会问题一面,贡献特别大,影响特别深。从民九起,国家教育设计,即已承认中小学国文读本,必用现代语文作品。因此梁任公、陈独秀、胡适之、朱经农、陶孟和……诸先生在理论问题文中,占了教科书重要部门。然对于生命在发展成长的青年学生,情感方面的启发与教育,意义最深刻的,却应数冰心女士的散文,叶圣陶、鲁迅先生的小说,丁西林先生的独幕剧,朱孟实先生的论文学与人生信札,和佩弦先生的叙事抒情散文。在文学运动理论上,近二十年来有不断的修正,语不离宗,“普及”和“通俗”目标实属问题核心。真能理解问题的重要性,又能把握题旨,从作品上加以试验,证实,且得到持久性成就的,少数作家中,佩弦先生的工作,可算得出类拔萃。求通俗与普及,国语文学文字理想的标准,是经济、准确和明朗,佩弦先生都若在不甚费力情形中运用自如,而得到极佳成果。一个伟大作家最基本的表现力,是用那个经济、准确、明朗文字叙事,这也就恰是近三十年有创造欲,新作家待培养、待注意、又照例疏忽了的一点。正如作家的为人,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一个作家的伟大处,“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但是在一般人习惯前,却常常只注意到那个英雄气质而忽略了近乎人情的厚重质实品性。提到这一点时,更让我们想起“佩弦先生的死去,不仅在文学方面损失重大,在文学教育方面损失更为重大”;冯友兰先生在棺木前说的几句话,十分沉痛。因为冯先生明白“教育”与“文运”同样实离不了“人”,必以人为本。文运的开辟荒芜,少不了一二冲锋陷阵的斗士,扶育生长,即必需一大群有耐心和韧性的人来从事。文学教育则更需要能持久以恒兼容并包的人主持,才可望工作发扬光大。佩弦先生伟大得平凡,从教育看远景,是惟有这种平凡作成一道新旧的桥梁,才能影响深远的。
我认识佩弦先生本人时间较晚,还是民十九以后事。直到民二十三,才同在一个组织里编辑中小学教科书,隔二三天有机会在一处商量文字,斟酌取舍。又同为一副刊一月刊编委,每二星期必可集会一次,直到抗战为止。西南联大时代,虽同在一系八年,因家在乡下,除每星期上课有二三次碰头,反而不易见面。有关共事同处的愉快印象,照我私意说来,潘光旦、冯芝生、杨今甫、俞平伯四先生,必能有纪念文章写得更亲切感人。四位的叙述,都可作佩弦先生传记重要参考资料。我能说的印象,却将用本文起始十余字概括。
一个写小说的人,对人特别看重性格。外表轮廓线条与人不同处何在,并不重要。最可贵的是品性的本质,与心智的爱恶取舍方式。我觉得佩弦先生性格最特别处,是拙诚中的妩媚,即调和那点“外润而内贞”形成的趣味和爱好。他对事,对人,对文章,都有他自己意见,见得凡事和而不同,然而差别可能极小。他也有些小小弱点,即调和折衷性,用到文学方面时,比如说用到鉴赏批评方面,便永远具教学上的见解,少独具肯定性。用到古典研究方面,便缺少专断议论,无创见创获。即用到文学写作,作风亦不免容易凝固于一定风格上,三十年少变化,少新意。但这一切又似乎和他三十年主持文学教育有关。在清华、联大“委员制”习惯下任事太久,对所主持的一部门事务,必调和折衷方能进行,因之对个人工作为损失,对公家贡献就更多。熟人记忆中如尚记得联大时代常有人因同开一课,各不相下,僵持如摆擂台局面,就必然会觉得佩弦先生的折衷无我处,如何难能可贵!又良好教师和文学批评家,有个根本不同点:批评家不妨处处有我,良好教师却要客观,要承认价值上的相对性,多元性。陈寅恪、刘叔雅先生的专门研究,和最新创作上的试验成就,佩弦先生都同样尊重,而又出于衷心。一个大学国文系主任,这种认识很显然是能将新旧连接文化活用引导所主持一部门工作,到一个更新发展趋势上的。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若还需要办下去,佩弦先生这点精神,这点认识,实值得特别注意,且值得当成一个永久向前的方针。
凡讨论现代中国文学过去得失的,总感觉到有一点困难,即顾此失彼。时间虽仅短短三十年,材料已留下一大堆。民二十四年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人赵家璧先生,印行新文学大系,欲克服这种困难和毛病,因商量南北熟人用分门负责制编选。或用团体作单位,或用类别作单位。最难选辑的是新诗。佩弦先生担任了这个工作,却又用的是那个客观而折衷的态度,不仅将各方面作品都注意到,即对于批评印象,也采用了一个“新诗话”制度辑取了许多不同意见。因之成为谈新诗一本最合理想的参考读物,且足为新文学选本取法。
佩弦先生的《背影》,是近二十五年国内年青学生最熟习的作品。佩弦先生的土耳其式毡帽和灰棉袍,也是西南联大同人记忆最深刻的东西。但这两种东西必需加在一个瘦小横横的身架上,才见出分量,——一种悲哀的分量!这个影子在我记忆中,是从二十三年在北平西斜街四十五号杨宅起始,到“八一三”共同逃难天津,又从长沙临时大学饭厅中,转到昆明青云街四眼井二号,北门街唐家花园清华宿舍一个统舱式楼上。到这时,佩弦先生身边还多了一件东西,即云南特制的硬质灰白羊毛毡。(这东西和潘光旦先生鹿皮背甲,照老式制法上面还带点毛,冯友兰先生的黄布印八卦包袱,为本地孩子辟邪驱灾用的,可称联大三绝。)这毛毡是西南夷时代的氆氇,用来裹身,平时可避风雨,战时能防刀箭,下山时滚转而下还不至于刺伤四肢。昆明气候本来不太热太冷,用不着厚重被盖,佩弦先生不知从何时起床上却有了那么一片毛毡。因为他的病,有两回我去送他药,正值午睡方醒,却看到他从那片毛毡中挣扎而出,心中就觉得有种悲戚。想象他躺在硬板床上,用那片粗毛毡盖住胸腹午睡情形,一定更凄惨。那时节他即已常因胃病,不能饮食,但是家小还在成都,无人照顾,每天除了吃宿舍集团粗粝包饭,至多只能在床头前小小书桌上煮点牛奶吃吃。那间统舱式的旧楼房,一共住了八个单身教授,同是清华二十年同事老友,大家日子过得够寒伧,还是有说有笑,客人来时,间或还可享用点烟茶。但对于一个体力不济的病人,持久下去,消耗情形也就可想而知。房子还坍过一次墙,似在东边,佩弦先生幸好住在北端。
楼房对面是个小戏台,戏台已改作过道,过道顶上还有个小阁楼,住了美籍教授温特。阁楼梯子特别狭小曲折,上下都得一再翻转身体,大个子简直无希望上下。上面因陋就简,书籍、画片、收音机、话匣子,以及一些东南亚精巧工艺美术品,墙角梁柱凡可以搁东西处无不搁得满满的。屋顶窗外还特制个一尺宽五尺长木槽,种满了中西不同的草花。房中还有只好事喜弄的小花猫,各处跳跃,客人来时,尤其欢喜和客人戏闹。二丈见方的小阁楼,恰恰如一个中西文化美术动植物罐头,不仅可发现一民族一区域热情和梦想,痛苦或欢乐的式式样样,还可欣赏终日接受阳光生意盎然的花草,陶融于其中的一个老人,一只小猫,佩弦先生住处一面和温特教授小楼相对,另一面有两个窗口,又恰当去唐家花园拜墓看花行人道的斜坡,窗外有一簇绿荫荫的树木,和一点芭蕉一点细叶紫干竹子。有时还可看到斜坡边栏干砖柱上一盆云南大雪山种华美杜鹃和白山茶,花开得十分茂盛,寂静中微见凄凉,雨来时风起处一定能送到房中一点簌簌声和淡淡清远香味。
朱自清
那座戏楼,那个花园,在民初元恰是三十岁即开府西南,统领群雄,反对帝制,五省盟主唐继尧将军的私产。蔡松坡、梁任公,均曾下榻其中。迎宾招贤,举觞称寿,以及酒后歌余,月下花前散步赋诗,东大陆主人的豪情胜概,历史上动人情景,犹恍惚如在目前。然前后不过十余年,主要建筑即早已赁作美领事馆办公处,终日只闻打字机和无线电收音机声音。戏楼正厅及两厢,竟成为数十单身流亡教授暂时的栖身处,池子中一张长旧餐桌上放了几份报,一个不美观破花瓶,破烂萧条恰像是一个旧戏院的后台。戏台阁楼还放下那么一个“鸡尾”式文化罐头。花园中虽经常尚有一二十老花匠照料,把园中花木收拾得很好,花园中一所房子中,小主人间或还在搁有印缅总督,边疆土司,及当时权要所送的象牙铜玉祝寿礼物堆积客厅中,款待客人,举行小规模酒筵舞会,有乐声歌声和行酒欢呼笑语声从楼窗溢出,打破长年的寂静。每逢云南起义日,且照例开放墓园,供市民参观拜谒。凡此都不免更使人感到“一切无常,一切也就是真正历史”。这历史,照例虽存在却不曾保留下来,保留下来的倒常常是“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诗人黍离的感慨!就在那么一种情形下,《毁灭》与《背影》作者,站在住处窗口边,没有散文没有诗,默默的过了六年。这种午睡刚醒或黄昏前后镶嵌到绿荫荫窗口边憔悴清瘦的影子,在同住七个老同事记忆中,一定终生不易消失。
在那个住处窗口边,佩弦先生可能会想到传道书所谓“一切虚空”。也可能体味到庄子名言:“大块赋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因为从所知道的朋友说来,他实在太累了,体力到那个时候,即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佩弦先生本来还并未老,精神上近年来且表现得十分年青。但是在公家职务上,和家庭担负上,始终劳而不佚,得不到一点应有的从容,就因劳而病死了。
广济寺下院砖塔顶扬起的青烟,这两天可能已经熄灭了。能毁灭的已完全毁灭。但是佩弦先生的人与文,却必然活到许多人生命中,比云南唐府那座用大理石砌就的大坟还坚实永久。
八月十九日西郊
(原载1948年8月28日《新路》周刊第1卷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