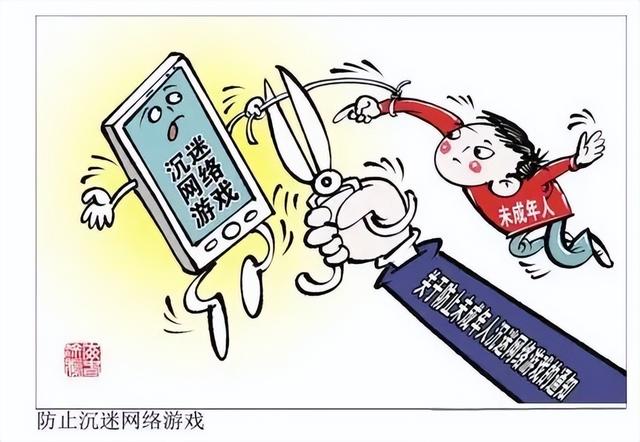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方的人群,又会形成一方的民俗每一方的民俗,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韵味比方说,故乡寿光的婚宴,就很有些与众不同之处,我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好吃的家乡味让你回味?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吃的家乡味让你回味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一方的人群,又会形成一方的民俗。每一方的民俗,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韵味。比方说,故乡寿光的婚宴,就很有些与众不同之处。
小孩子的天性,不光是贪玩,嘴馋也是。儿时回故乡,跟着爷爷奶奶去“坐席”,或者说是去吃“九大碗”,是我最为期盼的事情之一。相对于很多同龄人,虽说我的儿时生活并不缺衣少食,但婚宴上品种比较丰富的菜品,依然对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毕竟,那是一个贫穷而紧缺的年代。因而,偶尔的丰富,就显得弥足珍贵。不像现在,哄小孩子好好吃饭,几乎成了城市人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
在故乡的民间,婚宴俗称“九大碗”。因而,乡亲们通常把赴婚宴,称之为去吃“九大碗”。所谓“九大碗”,就是用粗瓷大碗盛着的九道菜品。用粗瓷大碗作为婚宴器皿,也算是一种与众不同之处。比方说,我曾在淄博工作过一段时间,那儿的人们办婚宴,凉菜用平盘、热菜用汤盘,还有专门的鱼盘、汤盆等等,很是有范儿。淄博是陶瓷之乡,婚宴习俗自然会有陶瓷文化的印记。
各地婚宴上的菜品,一般都是讲究双数的,成双成对嘛。而故乡“九大碗”的婚宴习俗,究竟起源于何时、又有些什么特别的来历和说法,我没有进行过考证,因而不甚了了。但是任何一种习俗的形成,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我想,在这里边,大约是寄托了一种“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吧。
故乡的“九大碗”,看上去不够精细讲究,但却透着亲切和实在。民间的婚宴,图个热闹喜庆随和,也就够了。如果弄得太讲究、太规矩,就有可能让人产生疏离拘束之感。再者说,办婚宴、吃婚宴的人那么多,乱乱哄哄的,假如一不小心,把那么精致的盘子打碎几只,还不把主家心疼死啊。在那个贫穷紧缺的年代,盘子碟子之类的瓷器,对百姓来说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一般人家是舍不得用的,或者干脆就用不起。就是那些不值钱的粗瓷大碗,多数也是从邻居家借来应急的。
其他地方的婚宴,上菜顺序一般是先凉菜后热菜,再后是汤菜。比方说,我在淄博吃过的婚宴,就是先上几个凉盘,然后再上热菜,再后面是汤菜。而各种热菜的顺序,比如炒菜、炸菜、炖菜之类,也都有讲究。而故乡的“九大碗”,却只对四道菜的次序有硬性规定,所谓“一鸡二鱼三凉菜、碗底一块肉”是也。也就是说,第一道是鸡、第二道是鱼、第三道是凉菜、最后一道是大肉。至于中间几道,则可以丰俭由人,什么炒芹菜、炒豆芽、炒芸豆、炒土豆丝、韭菜炒鸡蛋、白菜炖豆腐之类,都成。
在紧缺年代,鸡和大肉都属于紧缺资源。至于鱼,可不是东星斑、苏眉、三文鱼之类的名贵鱼类,而是鲤鱼、鲫鱼、草鱼什么的。儿时的故乡池塘遍布、沟渠纵横,这东西算不得什么稀罕物,珍贵程度与鸡和大肉不能同日而语。
在当时的乡村,母鸡承担着下蛋换零花钱的重要任务,乡亲们有“半年糠菜半年粮,鸡腚眼子是银行”的说法。而公鸡和猪,通常也是为了卖掉换钱的,没人舍得杀了吃,何况公鸡还有打鸣的职责。只有那些得了瘟病要死的鸡,主人才会无奈杀了解解馋。儿时假期回故乡的时候,我就吃过大伯父家的瘟鸡,感觉一样香,比大窝窝头就大罗卜咸菜好吃多了。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食品很不安全。但是说这话的人,肯定没有经历过那个紧缺的年代,因而他们不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食品安全很重要,填饱肚子更重要。时常被饥饿困扰的人们,哪里有资格挑剔食物的品质啊。
至于海参、鲍鱼和鱼翅这类的高档菜,当时的乡亲们不要说吃,连听怕是都没听说过。因而,鸡和大肉这两道婚宴上最硬的菜,自然应当放在开头和结尾的位置。把开头吃高兴、给结尾留想头,这样的安排,想想确实比较有道理。
“九大碗”中的鸡,不是烧鸡、扒鸡、炒鸡之类,而是“虎头鸡”。“虎头鸡”的制作方法,也颇为别具一格。先是将鸡肉剁成寸丁小块,裹上用鸡蛋和面粉调成的芡,入油锅炸至七八成熟备用。然后,再配以松蘑、山药等辅料炖熟。在故乡,“虎头鸡”这道菜品,也常被人们用作春节待客。
儿时跟爷爷奶奶回故乡,沾了爷爷在族人中“辈高望重”的光,我常常跟了他们去吃“九大碗”。故乡的乡亲们,赴婚宴一般都是不带孩子的,怕人家背后里说闲话,讥笑自家占别人便宜。但是老年人通常都会犯选择性宠爱的毛病,比如爷爷奶奶。在软磨硬泡之下,我一般都会成为婚宴桌上的例外。
故乡人办婚宴,都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支起大棚子,架上几口大锅开炒。以当时的条件而言,且不论乡亲们有没有钱去酒店办婚宴,就是想去,乡间也找不到这样的场所不是。大厨炒菜的浓浓香气,从锅里蒸腾而上,溢出院子老远,闻着都能让人馋涎欲滴。一些与我同龄的人都说,如今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刺激起自己的食欲。而我每当闻到炖大肉、炒芹菜、炒豆芽之类的味道时,还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但是我知道,那样的反应,其实是源于乡思,而并非食欲。
婚宴的宴席,则设在自家和四邻家的堂屋里。一张八仙桌,围坐八个人,年高德劭者居上。在婚宴上,爷爷奶奶都会让我站在他们旁边,而不让我自己占一个座位。他们还会语含歉意对别人解释说,“这孩子眼生缠人,回老家来一趟一步也离不开我们。”乡亲们倒不以为意:“没事没事,人家城里孩子啥没吃过、啥没见过啊,咱这庄户饭人家能看得上眼就不错了。”
婚宴设在晚上而不是时下流行的中午,也是故乡婚俗比较独特的地方。这么做,是为了给制作“九大碗”留出足够的时间,还是为了配合闹洞房的喜庆气氛?不得而知。无独有偶,我女儿出嫁的时候,她的公婆按照浙江萧山乡间的习俗,也是把婚宴放在了晚上。这样一来,就辛苦了那些其它村子前来贺喜的亲友们——喝完喜酒还要赶夜路回家。好在那时的人们都相互体谅,对于宴席上的酒,没人好意思放开肚皮猛喝,而是心照不宣地抿两口意思意思算完。毕竟酒属于高消费品,而大家又都很贫穷,如果喝得主家拿不出酒来,那就尴尬了。所以,婚宴上的气氛,很是祥和融洽。没有吆五喝六,没有撒泼闹酒。婚宴结束之后,村里村外也看不到东倒西歪的醉汉。
在“九大碗”中,“虎头鸡”自然是我的最爱。盛在大碗里的“虎头鸡”块,圆润饱满,金黄油亮,香气扑鼻。染得碗里的松蘑、山药,甚至粗瓷大碗本身,也跟着泛出光、透着香。婚宴结束之后,主家通常会给四邻八舍送去一碗婚宴上的菜品品尝,意思是让大家都沾沾喜气,图个其乐融融的气氛。最讲究的送人菜品,也是“虎头鸡”。由此可见,这道菜在婚宴上的重要地位。
有些不爽的是,爷爷奶奶总是对我加以种种限制,不让我由着性子猛吃“虎头鸡”,并且他们几乎不动这道菜。起初,我以为爷爷奶奶不爱吃。后来才明白,他们是不想占用别人应该享用的份额。但让来让去的结果,“虎头鸡”还是入我的口腹最多。那些老旧的八仙桌,生生地被乡亲们围成了一方方浓浓的温情。这样的温情,当然会凝结为擦不掉、抹不去的记忆。
长大之后,德州扒鸡、四川口水鸡、歌乐山辣子鸡、新疆大盘鸡、广东盐焗鸡,以及这样那样的炒鸡炖鸡等等,我也吃过不少,但感觉都不如故乡的“虎头鸡”。这些花样繁多的鸡菜,香则香矣,也足够刺激,但感觉味道过于直接外露。而“虎头鸡”的香,虽然含蓄内敛,一点也不张扬,但却悠长醇厚,很耐回味,一如故乡的民风。
近些年来,我经常问故乡的年轻人,还知不知道“九大碗”婚宴的习俗。让人惆怅的是,不少人已经说不出个所以然了。少数知道的,也只是从长辈的口中听说过而已。随着手中金钱的宽裕,如今故乡已经基本没人在家中操办婚宴了。不差钱的,去豪华大酒店办。条件一般的,起码也得找家一般酒店应付场面。不然的话,会被人笑话的。而酒店里的婚宴,基本上已经标准化了。于是,“九大碗”也就慢慢变成了人们记忆中的一个名词。这也难怪,在金钱的强力冲击之下,哪里的习惯不改变,哪里的民俗不消亡?
多样的民俗,才能构成丰富多彩的生活。民俗的消亡、人们生活习惯的趋同,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于是我有时就会突发奇想,退休之后回故乡开一家专门操办“九大碗”婚宴的酒店,以民俗为独特卖点,会不会勾起人们怀旧的思绪,从而火爆一把呢?我也明白,这样的念头,充其量也就是想想而已。不是多么渴望发财,还是源于乡思。
随着时光逝去的,不只是我的年华,还有我的亲情。它所留下的,只是一些并不那么完整的记忆。如今的故乡,已经成为了我梦中才常常会去的地方。乡思与乡愁,不但关乎土地、关乎亲情,也关乎民俗。所以,我的乡思与乡愁,不但埋藏在心底,也常常泛起于舌尖。
壹点号谷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