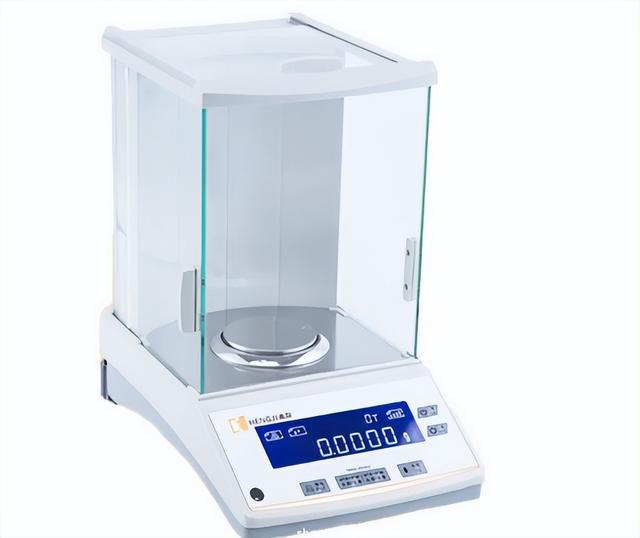课本中的“张衡地动仪”最近成了舆论关注的焦点。
先是有报道称,2017年投入使用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材七年级上册中,关于张衡地动仪的内容被删除。随后,人教社否认该消息,称课本中对地动仪有专门介绍。这引起了网友对地动仪的讨论。
那么,历史上真的存在地动仪吗?地动仪的复原又有什么样的故事?
史料中的地动仪
首先,关于地动仪,历史上确有记载,而且这样的记载见于多部史书。
2006年,中国科学院教授冯锐等人在文章《地动仪史料和模型研究》中集纳了涉及地动仪的历史资料。
教科书中张衡的形象。
文章统计,自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范晔完成《后汉书》,撰写东汉史书的共有13家,其中涉及地动仪并今天可见的史料包括司马彪《续汉书》、袁宏《后汉纪》以及范晔《后汉书》。
这些史料中关于地动仪器形的记载大体相同。
三部书中都记载地动仪“圆径八尺”,形似“酒尊”。东汉一尺约24厘米,以此推算,地动仪直径接近2米。
出土的汉代酒尊形制。图片来源:《地动仪复原模型的造型设计》截图
关于地动仪“盖”的记录,三部史料基本相同,有说“合盖隆起”,也有说“合盖充隆”、“其盖穹隆”。总之就是上端的盖要隆起。
同时,书中皆载,地动仪“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承之”。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地动仪外有八条龙,每条龙下面对应一只蟾蜍。
而关于内部构造,三书均称,“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这里明确,地动仪的内部有“都柱”,并通过“傍行八道”触动其中的机关,反馈地震方位。
关于地动仪长相的N个猜测
由于史料中的记载文字颇为简练,且至今未发现存世的地动仪图片,这为后世的复原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
也正因此,对于已复原出的地动仪来说,从不缺少争议。
按王振铎的考证,近代复原地动仪最早的是日本人服部一三。有记载显示,他在1875年就对地动仪外形进行了复原。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服部一三将地动仪设计成类似桶状,立雕的龙头和蟾蜍已基本符合今天人对地动仪的认知。
此后,英国地震学家米伦也尝试了对地动仪的复原。在1883年出版的《地震及其他地动》一书中,收录了他对地动仪的复原图式。他的设计采用悬垂法,并将悬摆突出到仪体外端。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而中国近代可考的对地动仪的复原,始于建筑师吕彦直在1917年发表的设计图。从图式来看,其复原的地动仪基本与米伦所复原的式样相同,只是对其艺术装饰和部分结构进行了补充。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到1936年,考古学家王振铎已对地动仪进行复原。该复原器外形看起来更像一个瓶,“瓶”外不见全龙,只有龙头,即便是从外观上看,和十几年后王振铎重新设计复原的地动仪有较大差别。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王振铎自己也在此后的文章中否定了这版地动仪,并称是“初步的尝试”且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因袭了米伦悬摆的推断,对倒摆认识不足,故复原成了复合悬摆”。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1937年,日本地震学家萩原尊礼尝试尝试复制地动仪的内部构造,并以“近代的无定向倒摆”原理解释仪器测震的原因。
两年后,日本地震学家今村明恒对近代复原的地动仪进行分析,并在萩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设计。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不过这两款日本专家设计的地动仪主要对内部构造进行了探索,外观并未严格按照史料中记载来制作。尤其是今村明恒的设计,基本没有一般人想象的地动仪外观。
1951年,王振铎基本推翻了自己1936年复原的地动仪,重新设计了一版。这次的复原作品后来被收录到课本中,也成为了大多数人记忆中地动仪的样子。
图片来源:王振铎《张衡候风地动仪的复原研究》截图
探索从未停止
王振铎1951年复原的地动仪采用“直立杆原理”。但这样的复原并非完美。
《华西都市报》的报道指出,王振铎虽然根据古籍记载复原出了地动仪的模型,但是因为模型内部结构缺乏合理性,所以其龙口中的铜丸无法吐下来,也就无法检测地震。
这以后,专家们对于地动仪复原的探索也并未停止。
图片来源:《地动仪的史料和模型研究》截图
物理学家李志超1994年提出自由杆模型。王湔则借鉴了现代地震仪的垂直摆结构,设置了4个重摆锤,再通过一系列装置触发直立杆倾倒。
图片来源:《地动仪复原模型的造型设计》截图
2009年,正式开馆的中国科技馆新馆展示了新的地动仪模型。该模型由中国科学院教授冯锐团队复原。
观众可以亲自动手按下按钮,观察在不同波型下地动仪的不同反应——只有横波到来它才吐丸,其他来自纵波的震动,都无法使地动仪有任何反应。这意味着,类似关门、汽车过境、巨大的炮声等都不会干扰到地动仪。
不过有报道指,学界对这一版本的模型同样存在质疑。
冯锐及其团队在一篇相关论文中这样写道,“19世纪服部一三把文字变成了猜想图形,20世纪王振铎把图形变成了展览模型”,而复原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深化认识、不断逼近历史的过程”。(记者 宋宇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