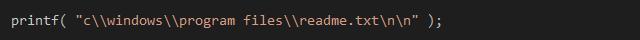文/暖风浅浅。
过了一个夏天,我开始收拾我的橱柜,本来只想把厨柜腾出一个地方,然后把刚刚整理好的面粉放进去,结果一看厨柜里的篦子,傻眼了!
这些用野高粱做的篦子,经过一个伏天也都吸收了空气中的潮气,篦子上有一层绿色的霉菌。我开始把篦子清理出来,并在水龙头上刷洗。
把洗洁精稀释到一种浓度,然后开始用刷子清理,我的天,不刷洗不知道,一刷洗竟用了半天的时间,一个个数过去,竟然也有十五六个,而这些篦子大多是母亲送给我的。有极少数是家里亲戚送的。
看到这篦子,第一时间便想起母亲,母亲的活可以说很精致,留在篦子上边的线几乎看不到。但如果认真去看,一行行密密匝匝的针线整整齐齐地排列着,让人一眼便看出做工的高级。
说起这篦子,总有一段让人啼笑皆非的事,这话得从头说起,从母亲出嫁说起。
母亲17岁就嫁给了我的父亲,嫁到家里,我的奶奶就让我的母亲用野高粱秸秆做篦子。母亲哪里会呀,这事可把母亲憋坏了,找我的外祖母去吧,还不好意思,新媳妇又怕被婆婆笑话,只好扎下头皮拿起针,穿上线,动作慢慢腾腾的,因为母亲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做。
我奶奶看着自己的新媳妇,心里在想,这媳妇做活真慢,还是离开这里,也许新媳妇就不会拘束了。想到这里,奶奶就离开了,只剩下母亲一人坐在院子里。
母亲瞅着这光光滑滑的高粱秸秆,不知道从何下手,索性就用针线把高粱秸秆一个个串起来,这样,一条长长的高粱秸秆整齐划一地排着队,我母亲还以为自己做得对呢!
当奶奶过来后,看到母亲做的篦子,就说:“这就是你做好的篦子?”
“嗯,是呀!”母亲答道。
奶奶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声让母亲不知道做的对还是不对,奶奶捂着嘴笑着弯下腰,从母亲做的篦子里找到针线,然后把篦子挑起来,一条高粱秸秆排着队,奶奶笑着说:“这叫孩子玩的赫朗朗,怎么能叫篦子?”
母亲一听傻了眼,感觉我奶奶嘲笑了她,扔下正在做的工作,一溜烟跑回了娘家。
到了娘家,外祖母就问她,出了啥事,这么慌里慌张的?这不问还好,一问母亲却哭了,说我奶奶看不起她,故意让她出丑。
外祖母把问题问清楚后,就开始教母亲做高粱篦子,母亲从这以后,才学会做篦子。在母亲的心里有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不能让我奶奶笑话她这个儿媳。
当母亲做篦子的手工活做得很不错的时候,奶奶再也不说母亲做的篦子是玩具,母亲也以此为荣。
每当秋季的时候,母亲就会做上几个高粱秸秆做的篦子,她做的篦子是非常圆的,针脚很小,可以说等同一件艺术品。等我结婚后,她把自己做的篦子让我带回去,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把母亲送的篦子珍藏起来,没想到今天细细数来已经有十几个了。
每当母亲给我篦子的时候,母亲就会给我讲结婚后做篦子的事,虽然年代已经久远,但这故事我总是百听不厌。每次谈起这事,母亲总是开怀大笑,而我也总是说母亲做的篦子是当时村子里家喻户晓的笑话。
去年冬天的时候,有一位远房姐姐给了一把高粱秸秆,我把这把高粱秸秆放在了母亲那里,让她有时间的时候为我做一个篦子,母亲爽快地答应了我。
当母亲把做好的篦子拿给我的时候,我的心流泪了。因为篦子的针脚是如此的大,而且显然没有以前做的篦子精致,歪歪扭扭的线让我看到母亲一双眼睛已经变得不明亮了。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她答应我的时候很爽快,其实她的眼睛和手已经不协调了。即便如此,母亲仍然愿意为儿女们做些什么。
我没有买过篦子,用的篦子都是母亲做的。在我的眼里,母亲做的活是一流的做工。可岁月不饶人,母亲已不在年轻,从她的白发里我读懂了岁月,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了一颗慈母的心。
又到秋季了,我看着满院的篦子,心里生出的是酸楚的泪。母亲的腰板不在挺拔;母亲双腿走起路来已是像蹒跚学步的孩子;母亲看到我总是满眶的热泪相涌;她嘴角一撇就像是几年没见过我似的。相见时,我与母亲的手总是十指相扣或者紧紧地搭在一起,在无言里默默相视。
我轻轻用手试去母亲的泪痕,那滚烫的热泪捂热了我的手心,也捂热了一颗女儿的心。我停靠在母亲的怀里,永永远远都想依偎。
看着满院的篦子,我的心久久不能释怀。秋风吹动着篦子,篦子在秋阳下旋转着,就像母亲的一颗心不停地跳动。我轻轻地用手托起篦子,深情地对篦子送上一个长吻!
~~~~~~~~~~~~~~~~
我是暖风浅浅,《竹海文艺》的签约作者,简书的创作者。我以我笔书情怀,品人生百味,说人间烟尘。我在这里与你一起分享生活,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评讨论。
#我要上#
#「闪光时刻」主题征文 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