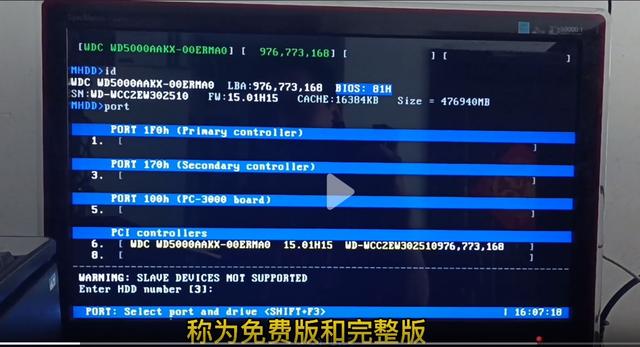1978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在文艺版面上刊登了一则电影资讯,称:“今年元旦,全国上映了由长春、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两部彩色故事片,一部是《熊迹》,另一部是《青春》。”
对《熊迹》,这则资讯介绍如下:“《熊迹》是一部反特故事片。影片以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至一九七二年秋为历史背景,描写了以李欣为代表的公安战士,在党的领导和群众帮助下,破获一起盗窃我国重要战略情报的重大间谍案件的故事。
这部影片结尾,谢尔丘克等间谍被驱逐出境了,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十二年前离开我国的某国间谍彼得洛夫又被派到北京来了,斗争仍在继续。影片形象地告诉人们,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把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的斗争进行到底。”
《熊迹》拍成于1977年,而实际上,它的筹备时间,当上溯到1974年。
1974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篇通讯《苏修间谍落网记》,这篇通讯,正是《熊迹》的故事源头。
《苏修间谍落网记》的作者署名为新华社记者。那么,它的执笔者谁?
《熊迹》的编辑署名为巩卓。根据当时出现的反特文艺作品的规律,这显然是一个笔名:公作,也就是公安部门的创作者所创作。
相类似的是,源出于新华社记者所撰写的通讯,于1975年2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苏修间谍落网记》的绘画作者署名为龚梅。谐音的意思是:公美,即公安部门的美术工作者。
类似的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的小说《红石口》作者署名为:龚成,谐音的意思是:公成,即公安部门的成员组成。这部小说的实际作者是由公安部门的樊斌、迟滨光分头写出初稿,然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子敏、崔道怡修改统稿。
《东港谍影》据以改编的小说《斗熊》出版于1976年5月,署名为:尚弓,谐音意思是:上公,即上海公安部门的创作人员,具体写作成员包括:陈镇江、周云发、牟怀珂、李春茂、沈霞。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段时期内涌现出的反特小说里,其幕后大佬,都有苏联的影子。而这些小说作品,都可以追溯到《苏修间谍落网记》这篇发表于1974年1月23日的通讯。
可以说,1974年1月23日的这篇通讯的发表,揭开了苏联特务操纵的幕后阴谋的黑盖,引发了当时中国文艺界对这一题材的批量创作。
《苏修间谍落网记》这篇通讯,没有署名作者。但据刊发在1998年5月号的《人民公安》杂志上的《王文林:写电影的人》介绍,《苏修间谍落网记》的作者是王文林与新华社著名记者穆青合作完成。
而电影《熊迹》,也是出自王文林之手。
据王文林自己介绍:““我写的电影《熊迹》(署笔名‘公卓’)是1974年4月总理住院前夕交给我的任务。遗憾的是4月份总理住院后再也没能出院。”
由此可以看出,《熊迹》剧本的创作时间,几乎紧跟着《苏修间谍落网记》这篇通讯,就开始了动笔。在1974年12月,它就完成了剧本初稿。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在这个剧本的初稿本上,标明的时间正是1974年12月。
但拍摄的时间,一直拖延到1977年。它公映的时候,也是中苏关系的由敌对转为正常的一段微妙的时间。在之后的反特题材或者叫谍战题材的创作中,像《熊迹》这样,把苏修特务作为矛头指向的文艺作品,基本绝迹。
《熊迹》开拍于1975年,一直到1977年才真正拍完,然后在1978年元旦上映,其拍摄周期之长,简直难以置信,但也说明这个题材之重大,拍摄人员不得不慎之又慎。
现在看来,《熊迹》与据以改编的原型通讯《苏修间谍落网记》的差别还是巨大的。《苏修间谍落网记》里作为重点部分进行描写的苏修特务落网的过程,在《熊迹》里只有在最后五分钟内轻描淡写地予以了再现。而《熊迹》的故事情节的侧重重点,倒不是这个最后的苏修 间谍落网的惊心动魄的时刻,反而是放在了国内的间谍侦破记。
这根本性的问题,是原型故事中的苏联派遣间谍李洪枢在一进入中国境内,就被抓住,根本没有活动的空间与时间,而在《熊迹》里,却通过这个潜入间谍的线索,拔出萝卜带出泥地拉扯出国内的一串潜伏间谍。
这种结构,也是当时类似的境外间谍入境后的反特题材文艺作品的共同特征,这些作品,对境外势力的描写反而是一种背景状态,而主要表现的是国内的潜伏特务的暴露,构成了这类文艺作品的共同的表达终极胜利的架构模板。
这主要原因是这类反特题材的文艺作品的主要题旨功能,仍然是在图解“阶级斗争”这个主题,用以证明国内的阶级敌人,配合亡我之心不死的境外势力在作着最后的鱼死网破的疯狂。
《熊迹》的故事发生地放在哈尔滨。电影里的苏联特务的主要目的,是打探“八一四”战备工程的图纸信息。而这个工程,据资料介绍,是以哈尔滨市的“7381”工程为原型。
据《哈尔滨市志》介绍,这个工程是1973年8月1日决定筹建的,故定名代号“7381”工程。为了取得建设较大规模工程建设的经验,1974年2月,在哈尔滨市东郊荒山组织试验段工程施工,取得经验后,于1975年2月开始从东大直街省军区院内正式施工,陆续延伸到和兴路、动力区进乡街。到1979年末,因贯彻调整方针,经费受到限制,经省人防领导小组决定,工程停止延伸建设。
而苏修间谍李洪枢是从何时入境的呢?
我们在当时负责李洪枢案的公安部领导刘复之所著的《刘复之回忆录》中看到:1972年6月5日李洪枢入境。6月23日李到沈阳市某工厂找人。6月29日上午,宁安县东站出现了李洪枢,由他的堂妹带回家里落脚。这时,宁安县公安局果断地逮捕了李洪枢。
也就是说,真正的间谍原型李洪枢入境不到一个月就被抓住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打探什么情报。
而在李洪枢被控制住的1972年,当时的哈尔滨的“7381”工程还没有决定筹建。而据连环画《苏修间谍落网记》里的介绍,李洪枢并没有到过哈尔滨,只是在牡丹江市、佳木斯等地活动。因此,《熊迹》里把间谍案与“7381”工程拉扯上关系,只是编剧的创作需要。
而值得注意的是,《熊迹》的编剧王文林曾经参与了《铁道卫士》的创作。在《铁道卫士》里,也有公安人员冒充潜伏特务,打入敌人内部的情节,在《熊迹》里,也继承了这样的模式,其中表现了公安人员与苏联使馆人员在长城脚下进行了会面。实际上,《熊迹》里把《苏修间谍落网记》里的苏联使馆人员不能见人的进行间谍活动的丑闻,先期预演了一遍,由我公安人员早就与苏联大使馆人员进行了秘密接触,掌握了至关重要的潜伏间谍的身份。《熊迹》的故事情节曲折离奇,而《苏修间谍落网记》提供的原型情节却相对简单,可以看出,《熊迹》在原有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虚构性创作,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创作,虽然增加了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性,但是却打破了原来通讯提供的素材的架构。
这根本原因,还在于主抓李洪枢案的刘复之在回忆录中所说的那样,李洪枢被抓之后,我方对其进行了“逆用”,从而暴露出了幕后主使者的真正嘴脸。
这也是《熊迹》里由李默然扮演角色所陈述的主题,“这些人(国内的潜伏者)不过被历史潮流泛起来的渣子,我们千万不能让那些渣子挡住我们的眼睛,放过了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最凶恶的敌人。”
也就是说国内的潜伏的特务,只不过是渣子而已,真正的敌人,是来自于境外的亡我之心的凶恶势力。
这个主题,也是《苏修间谍落网记》里表达的主题,《熊迹》在这个地方,把它的主题拉到了《苏修间谍落网记》的主题上去了。
从电影的角度来看,《熊迹》算不上是一部成功的影片,甚至在当时就被批评为烂片。影片里的潜入境内的特务,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两个隐藏的特务身上,入境特务,只是激活了国内的深埋的老间谍。这与李洪枢案的牵连出苏联幕后支使者丑态的入境特务的重要性不可同日而语。而在《熊迹》中,与苏联使馆人员接头的也不是从国外潜入的入境特务,而是国内的隐名埋姓的深藏着的特务,这与《苏修间谍落网记》的主线完全是迥然不同。
可见,《熊迹》除了在结尾部分融入了《苏修间谍落网记》的主要情节线之外,即北京夜色下的秘密接头,还有它自身的情节设置需要。尤其是公安部门人员,与苏联使馆人员进行了先期接触,并由此探访出了国内的潜伏特务黑手究竟是何人,已经隐伏了李洪枢案从一开始就处于我公安部门的掌控之中这一“逆用入境特务”的真实的幕后真相。
《熊迹》的导演是曾经在六十年代拍出过今天看来依旧张弛相间、震撼人心的反特片《冰山上的来客》的导演赵心水,但进入七十年代后,赵心水的导演掌控能力,始终不能让人满意,一直没有拍出如同《冰山上的来客》这样的镜头处理娴熟、人物刻画到位、结构慎密精制的影片。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导演也会有一种功力下降的状况,犹如文学创作一样,过了创作高峰期之后,会给人一种一落千丈之感。
《熊迹》在结构上内容松散、节奏拖沓、人物造作。入境特务如何与潜伏特务接上头、又如何轻易地成为人防工程的司机这些关键的节点,都没有交代清楚。显然,编剧王文林在创作时面临着无法突破《苏修间谍落网记》提供的原始素材的困扰之中,毕竟,在拍摄《熊迹》的时候,《苏修间谍落网记》涉及的李洪枢案还没有披露出更多的幕后背景。
在这样的情况下,编剧王文林不得不在《熊迹》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国内潜伏特务的重点刻画上。王文林后来的情况,我们也在此略作概述。他在1978年《人民公安》杂志复刊时,参与了主持工作,后调至人民公安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其实,凭着他对特殊时期历史的了解,能够写出更多的揭示历史真相的文学作品,但查阅一下王文林的作品,会发现少之又少。我们可以在《公安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上看到他所写的一篇《论公安大学的校风》,算是一篇论文,没有看到他更多的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不能说是一件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