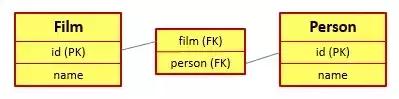中国神话里有龙,西方神话里也有龙,你知道,这两种龙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
闲时听到一位老者给少年讲画,此问一出,我也愣住。少年犹疑地回答:皮肤的颜色?脸部的神态?身姿的不同?
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颜色也好,表情也罢,各种细枝末节的不同都只是皮毛。
“中国的龙啊,都在腾云驾雾呢。”
老者并未故弄玄虚,登刻解了谜,可没再解释下去,少年尚有疑惑,我这旁听的人却恍然懂了。
西方电影里表现巨龙,从爪牙到胡须,从腹部褶皱到鳞片光泽,无一不清晰,无一不具体,毫发毕现,连肌肉动势都一清二楚。
而中国的龙啊,是极少愿屈尊降贵,显出全部真身的。在古时的画里,传说的本子里,龙总是掩在一团云雾中,堪堪露出一双额角,几只龙爪,一抹背部的龙鳞——
不需要更多,你就知道,这云山雾霭里,正有一只神龙,亟待冲天了。
图 | 蒽子-苏州
这是极具东方意蕴的表达。
含蓄着,氤氲着,朦胧着,隐约着。
雾里看花的,欲说还休的,懵懵懂懂的,仿佛微醺的。
因而,重要的,不是那条龙,重要的,是那团云雾。
云雾是活的,龙便是活的,云雾是死的,龙便是死的。
一座山若想有灵,不必真的神龙在天,只要有云流连,山便灵动。
一面湖若想有灵,不必真的巨龙在潜,只要有雾临湖,水便灵动。
就要看不清,就要道不明。就要亦真亦幻,就要若有似无。
偏也是这般依稀,这般宛若,这般好似,这般仿佛,让人莫名心动,方识大美。
图 | 梁木辛_
若要是说,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懂“雾里看花”之美,似乎大言不惭了些,那便谦虚着讲吧——关乎欣赏朦胧之美感,中国人的底子,确实更坚厚无疑。
是文化的熏陶,或也是土地的天赋,我们似乎天然就明白:迷离微茫,能产生比清晰直露更妙的美感。
图 | 梁木辛_
自古中国人欣赏山水,便以缥缈幽远为胜。
董其昌推崇米友仁的山水,将这云山墨戏视作一种“宇宙的游戏”,那《潇湘奇观图》里弥漫大片的淡墨,只在轻云间,叫树木留下恍惚的影,让山峦留下模糊的廓。这画会令人不自禁地幻想起,那天地初开,宇宙鸿蒙的样子。
图 | 蒽子-苏州
后来,士大夫造园林,怀揣的自然也是这般将缥缈山水移植庭院的心思。
那移步换景,游廊蹁跹,凿窗成画之力,好像就是要让人想起氤氲的云,想起迷离的雨,想起雾里的花,想起水中的月来。
抬头仰见的那些名字,什么“浮翠”,什么“香影”,什么“月到风来”,什么“寄啸山庄”,总是惹人在一片实景中,恍恍惚惚,思绪纷飞出无限虚意来。
图 | 蒽子-苏州
想起摄影师严明曾在书中写,如今影视进入高清时代,许多摄影师会追求极致清晰的细节,心心念念想要去表现它,甚至炫耀它,以为摄影真的是“看”的艺术,全然忘了这世界的美,“清晰”只是单一一项,除了真真切切,还有隐隐约约,如烟似雾,天地空灵,存乎一心。
敢于远,敢于虚,敢于不清不楚,敢于营造一个梦。
雾里看花,胜却人间无数。
图 | 蒽子-苏州
那团云雾,是雾里看花之造境,亦是欲说还休之余味。
欲说还休之处,正是最具张力之时,在这一秒,堪堪停住,方有无限回味的空间。
图 | 梁木辛_
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说,书法最要讲究的妙处,在“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意思是在书法中,起笔与落笔,皆要蓄势,如同白兔受惊的瞬间,起势若奔,却还未跑走——要有这“势”在,才有滋味,一笔平平到底,便毫无韵味可言。
一个好字,没有去了一笔是不回的,没有末了一垂是不缩的,没有一点是不隐藏锋芒的,没有一捺是没有内在折转的。书法的绵里藏针,就在于此,不懂的人看不出什么花哨,懂得的人心里已经波浪滔天。
图 | 蒽子-苏州
你可以认为这叫“含蓄”,但更准确的说法,大约是“欲说还休”。即便“休”了,你也知道,她是“欲说”的,欲说,则有无穷妙意可查探,可触碰,可揣摩。
将说而未说之际,是最具张力之时,是物理学中的临界点,一条曲线的顶端——想象面对心爱之人的欲说还休,犹如宇宙大爆炸的前一刻,不必向你展示下一秒是如何星河灿烂,山川耀眼,所爱之人山眉海目间的风月,足胜过眼之所及的一切。
图 | 蒽子-苏州
或也可证,为何初恋在心里,总是尤为动人。
因为初恋时,少年人懵懂,怯懦,连勇气都显得很笨拙。
如《人生海海》里写的那般:
初恋的感觉是甜蜜的秘密,是紧张的等待,偷窥,是手不经意中相碰触电的感觉,是炮声轰轰中的害怕和祷告,是午后的阳光在风中行走,是微风吹来了稻花香,是彻夜不眠的累人旅程,是各种复杂幽秘、别出心裁的明测暗探。
这是对于成年后在关系中摸爬滚打几番,个个都磨出七窍玲珑心的男女们来说,再难无知无觉倾情投入的游戏了。
图 | 蒽子-苏州
懵懵懂懂,迷迷糊糊,却有一股完完整整的精神气,如同一颗香气饱满的苹果,不必深究,只是见到,就有令人一见钟情的感染力。
而经历许多世事打磨之后,虽条理清晰,态度深刻,令人钦佩,却再难找回懵懂的魅力。
图 | 蒽子-苏州
我们喜唐诗胜过宋诗,或也是由此。
唐诗以韵胜,懵懂,浑雅,空灵,犹如将苹果放入口中,甜蜜的汁水迸射肆意的美,充分调动起人之情韵,不做深想,只愿奔赴一醉。
而走到宋代,诗不得已转向思理,情韵的自由空间所剩不多,虽不能说不好,总归不是浪漫。
图 | 蒽子-苏州
感知到朦胧时,常会觉得生活柔软了起来,有点像微醺时,觉得世事尽可原谅。
想起雨天在图书馆里坐,原本心情沉重,但就着雨窗,看到窗外远远近近的路灯亮起来,看到映在窗上圆圆濛濛的灯影,远处的树以默默的绿色衬在后面——一切都看不清晰,心里反倒漾出一股暖意,这扇朦胧,将雨天的凄冷隔绝开,氤氲出柔柔的气氛来。
图 | 蒽子-苏州
叶嘉莹恩师顾随讲中国文化,提到“氤氲”,说这两个字“写出来就神秘”,因与缊,都很老实,只是在头上加了“气”,邀来云雾,便混沌起来,有了妙义。
不得不感叹,如果未能识得那团云雾,那我该遗憾错过多少美。就像一个滴酒不沾的人,大约很难体会在一双醉眼里,这世界会变得怎样温柔可亲。
图 | 蒽子-苏州
有句诗写,叶底黄鹂音更好,隔溪烟雨醉时听。
诗人以为,聆听黄莺,当以浓荫深处传来的莺声为好,浓荫里的莺声,又以烟雨朦胧中为尤好,而烟雨莺声,又以醉时心境听之,为好中之好。
一层不够,又附上一层,视野里朦胧了,耳界里朦胧了,连意识也要朦胧了——这般莺声,才是唱给心听的。
图 | 梁木辛_
虽是看不清,虽是道不明,虽是亦真亦幻,虽是若有似无。
但胸膛里那颗心,却活跃起来,敏感起来了。
于是,便是这般依稀,这般宛若,这般好似,这般仿佛,让人雀跃心动,终于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