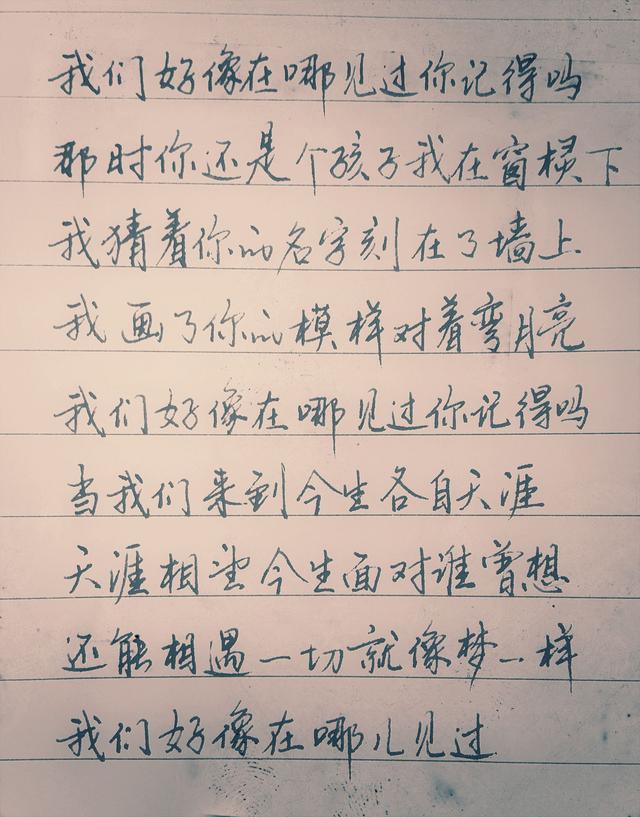文 | 出潼关
麦场打过麦之后,颗粒归仓。麦秸秆变得扁平发亮,被堆成垛,一个个圆形或方形的麦秸垛像小的蒙古包,坐落在麦场里、不占道的墙边。二十年前的老家,尚没有“村容村貌”一说,各家各户都有一个麦秸垛,麦秸是生火做饭最重要的燃料。
孩子们没有家庭作业,放学后丢下书包尽是玩耍,却也常被大人安排做一些活,比如在压水井上压水,到厨房里烧锅,背上粪箕子薅麦秸。压水是最省事的,像玩一样;烧锅耗时就较长,拉着风箱惦记着外面的伙伴,心里总是发急;若是跟薅麦秸比起来,所有的活都是轻松的了。
粪箕子是个笨重的器物,裸重七八斤。将粪箕子放在自家麦秸垛前,开始一把一把薅麦秸。新垛还好,一把就能薅出一大把,薅过几次之后,麦秸压得格外密实,下手都困难。抓住一把麦秸,使劲一薅,只能薅出很小的一把。有时,竖起手掌插进麦秸里,手指会被扎破,就越发使不上劲了。
大人们早教了我们装麦秸的方法:先把薅掉的麦秸同向扔在地上,看着差不多了,就开始装。先在粪箕子里面装上一排,粪箕子口处再装一排,要呈扇形展开,这样可以背回更多的麦秸。麦秸一定要压实,如果贪少贪快,很容易半路散落下来。
城里的老师给孩子们讲“打基础”的时候,都是讲大楼的地基,孩子们也未必见过;我的语文老师讲到这个词的时候,就问:咱们班的同学谁薅过麦秸?班里的孩子全都举起了手。老师接着说:你把粪箕子里下层的麦秸压结实了,才能一口气背到家,不然会散落下来,这就是打基础。我们马上都明白了。
压实的麦秸很重,粪箕子随着脚步一下一下撞着屁股,越走越累。这也比薅麦秸感觉好多了,厨房就是前方的梅林,背进厨房就可以出去疯玩了!一粪箕子麦秸就像我的战利品,骄傲地走在大街上。有上岁数的老人见了,会夸奖一句:小子没粪箕子高,能干着哩!
母亲深谙孩子天性,我薅了麦秸回来,就不会让我烧锅了。我将麦秸痛快地倒在厨房,忽然觉得身轻如燕,一个大步飞过门槛,在空中跟母亲说:刚才小杰的爷爷夸我来着。
“夸你啥?”母亲问。
“说我没粪箕子高,能干着哩!”我高声喊着,人已经跑出院子。
以沮丧接受,以痛苦完成,以解脱结束,薅麦秸让我完整地体会到苦尽甘来的过程。此后很多年,我经历了更多的事情,起初觉得充满了矛盾和困难,完成之后一身轻松,满心愉悦,想想跟薅麦秸是一样的。
我是个老实内向的孩子,这种性格表现在大人眼里就是听话。打针的时候,我咬着牙不哭出来;夏天孩子们都光着脊梁转悠,母亲说,你太瘦,光脊梁不好看,我也就成了唯一穿上衣的孩子;平均两天要被母亲安排去薅麦秸,尽管满心不想,却总会回答:哦。
我一直觉得,没有麦秸就吃不上饭,那些静静伫立的麦秸垛虽然可恨,却是极重要的。直到我上了四年级,才发现麦秸垛是我们快乐的城堡。
一天晚饭后,小军喊我去小要家玩。小要在青山上初中,是个孩子王。我们到他家时,已经聚集了七八个孩子,多数是我们班的。小要喝完最后一口汤,说:走,上麦场。一帮孩子欢快地出门了。
村西边有一块麦场,收过麦之后,堆起很多麦秸垛。月光如奶洗过一般,照在地上明晃晃的。这些麦秸垛错落有致,像独居老人的小屋。麦秸垛中间有大块的平地,小要让我们站成两排,教我们蹲马步,说这是练武的基本功。小要站在我们前面,蹲起马步,喊了声“一”,挥出左拳;“二”,收回左拳,同时挥出右拳。
“一,二;一,二……”我们跟着喊,照着做。
站马步太枯燥,小要也没有足够的耐心。他又开始教我们侧手翻,孩子们身体柔韧性好,很快掌握了技巧,我们兴奋地翻腾着,像一架架旋转的水车。
我们的身子很快就热了,开始在麦场上追逐打闹。随后又变成两伙,开始对打。几个孩子冲上麦秸垛,其余的孩子从下面发起攻击。上面的孩子被打下去,就飞速冲上另一个麦秸垛。麦秸垛上面是软的,双脚深陷进去;我们的身子也是软的,无论是挥拳,还是摔跤,都不觉得疼。我热得头发都湿透了,感觉谁都打不过我,不惧任何对手。我在垛顶被人一脚踢下,居然没有任何感觉,跑开十来米冲刺,一下子又冲了上去。
小要受了《少林寺》的影响,一心要练武,或许他并没有师傅,就成了我们的师傅。他告诉我们,练武要打好基本功,腿上要绑沙袋,要蹲着马步打沙袋。几天后,我用化肥袋子装了多半袋玉米,让父亲吊在树上,认真地打了几天,后来就觉得有些无味。我还用小的袋子装了黄沙,绑在两条小腿上。走到学校忍不住跟同学说,你看,我腿上绑着沙袋呢。
腿上的沙袋绑了多少天,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拿掉沙袋后,两条腿似乎没有任何负重,跑起来轻松如飞。
打麦场成为我们练武、打闹的乐园,麦秸垛成为我们攻守的城池,很多个夜晚,我们在追逐中跑掉了鞋子,在麦秸垛上的对打中撕掉了扣子。第二天在学校津津有味地回味,像讨论刚刚看过的武打片。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在打麦场坐成一圈,纷纷拿出从家里带的月饼、石榴、糖块,小振居然从裤兜里掏出半瓶白酒来。酒是没人喝的,我们分享着食物,觉得比家里的东西好吃多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有“练武”,大家吃完东西,小要说:走,咱听房去!麦场边上有一处新房,小杰的叔叔刚结婚。房子的后墙上,窗户底下,有一个麦秸垛。我们纷纷冲上去,仍够不着窗户,听不到一丝动静。小要说:你们喊“月经”。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纷纷朝着窗大声喊:月经,月经啦!或许小杰的嗓门太高,屋里忽然传来他叔叔的声音:小杰,滚回家睡觉去!
我们嬉笑着跑开,各自回家了。空旷的麦场上,只剩下一个个麦秸垛。
回忆起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们像低级的帮派组织。但仔细一想,小要从不允许我们做坏事,顶多只是调皮捣蛋些而已。在我们疯狂的追逐打闹中,从没有人急眼,也没有人受伤,却在贫困的年代享受到极大的乐趣。
小要上初三的时候,经媒人介绍跟同村的英子相了亲。当时我们都在院子里看,听到英子说:小要还害羞哩,脸都红啦!我们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小要你别害羞呀!小要从屋里走出来,涨红着脸说:小熊孩,滚!
我们哄笑着往外跑,小杰忽然扭头喊:小要,月经!
小要相亲不久就退学了。他跟我们说,跟英子见了面,回到学校就听不进课,光想她。初中退学是正常的事,小要退学不久就帮英子家收麦子,在麦场上堆起一个新的麦秸垛。
那年麦收过后,小要不让我们再去找他,说不能再祸害人家的麦秸垛。我们怅然若失。后来,我听小军说,他曾在麦场的麦秸垛下看到小要和英子,他俩亲嘴哩。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